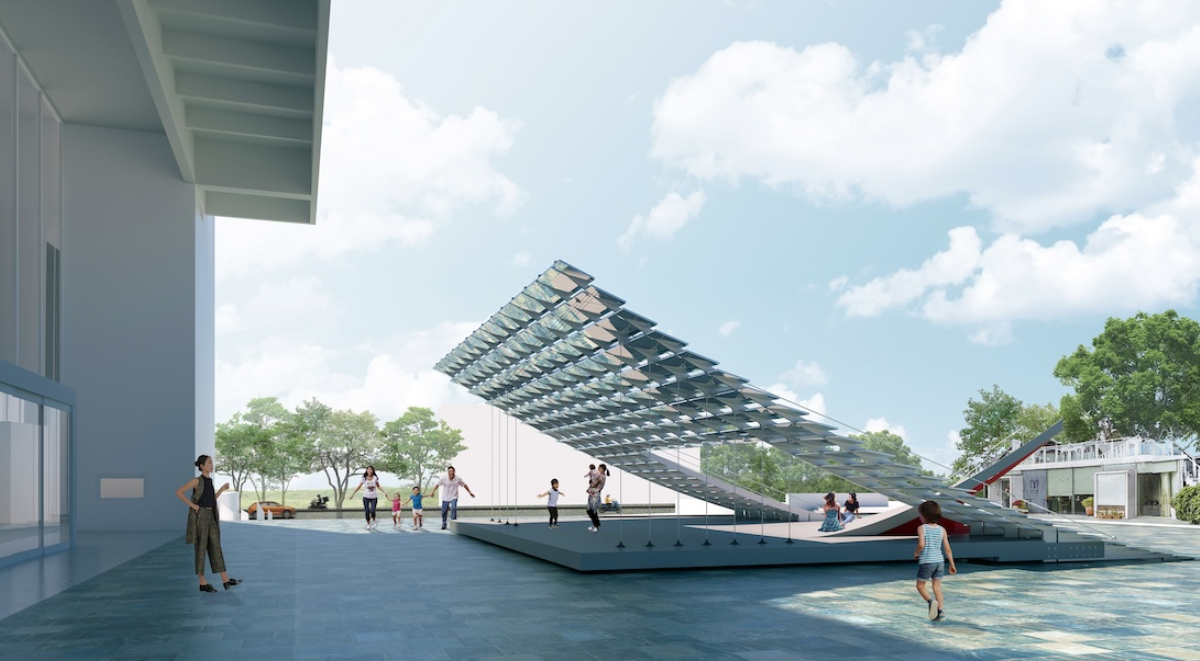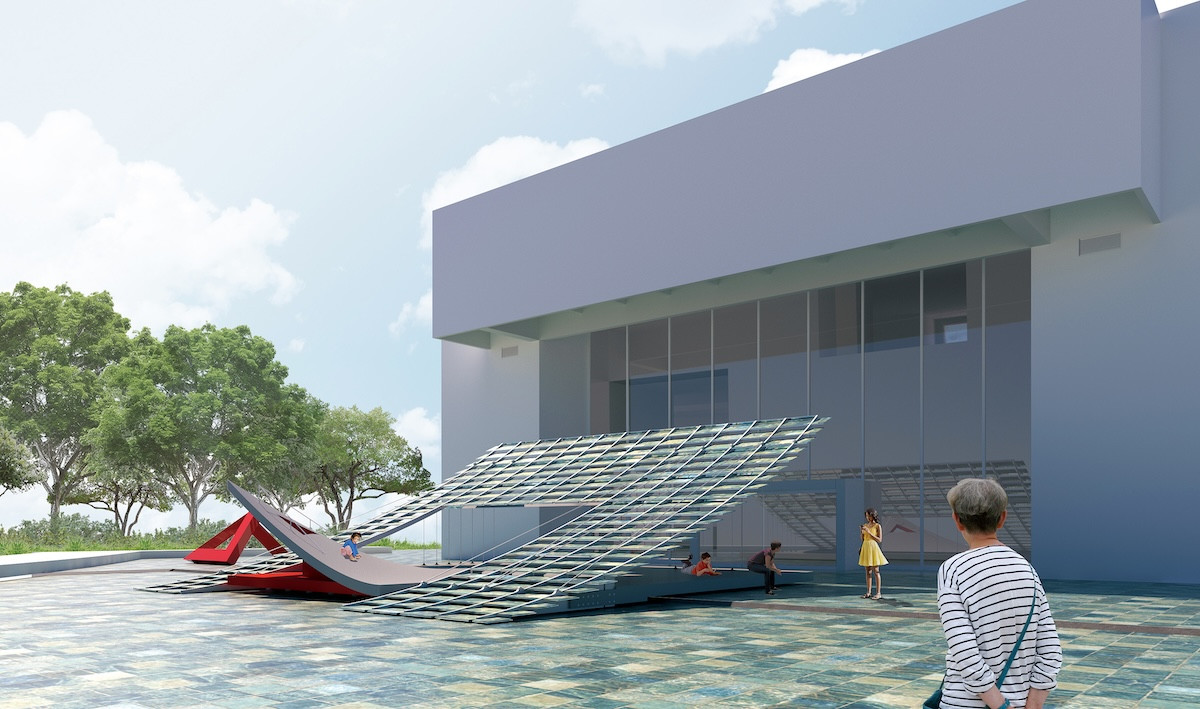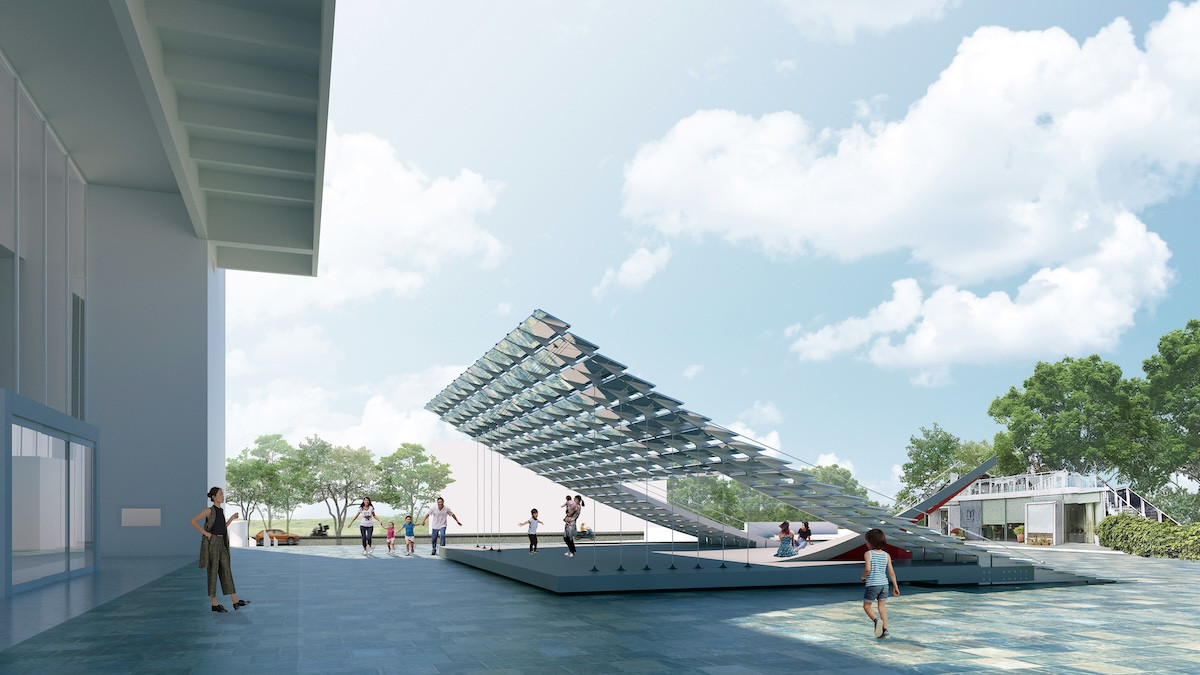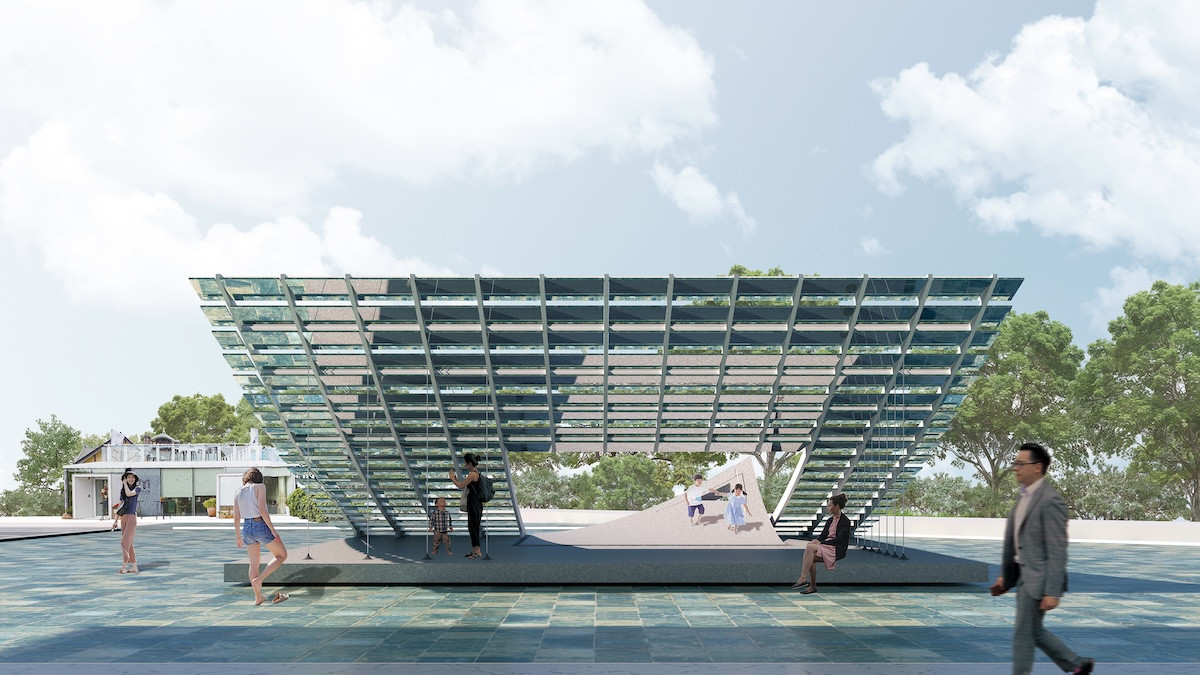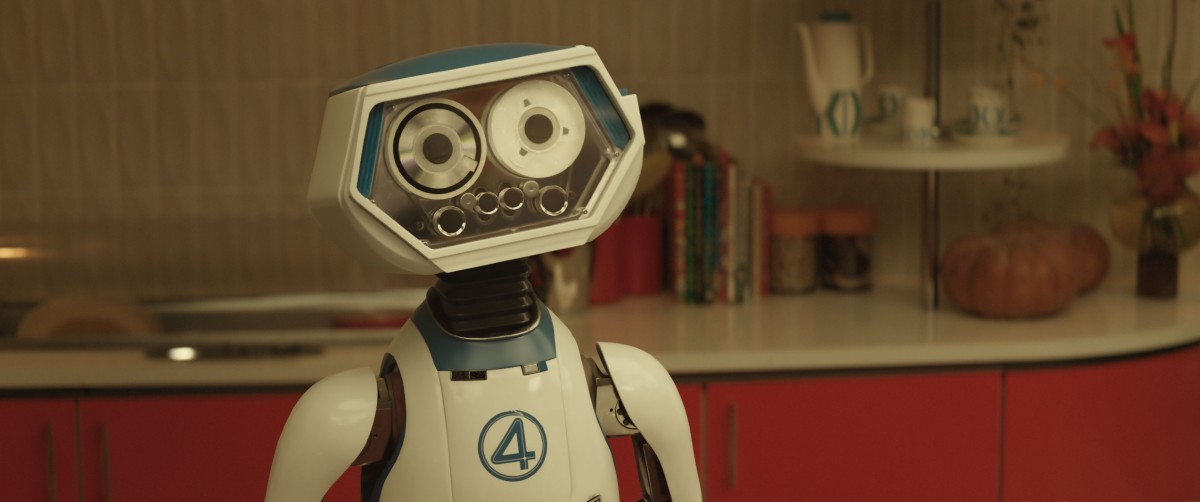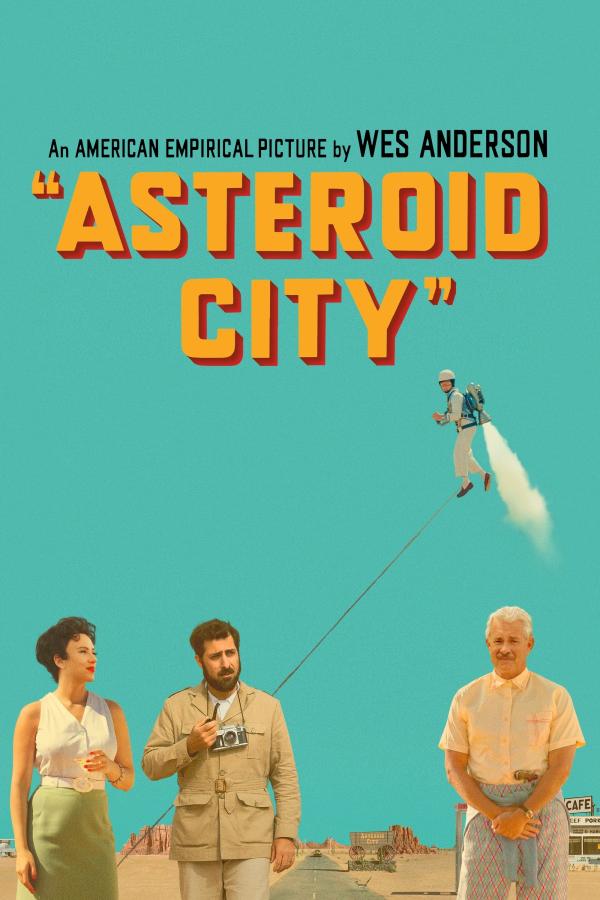《Game on》在2023年11月底晚間上演,地點是臺北表演藝術中心7樓的排練場;那陣子,我正好在重看《地獄廚房》(Hell’s Kitchen)。
不知道是追得太入迷、或這支舞作真的與廚藝實境秀共振,當下看舞者們跳著、拉扯著,腦中竟然默默浮現《地獄廚房》裡名廚Gordon Ramsay飆罵、廚師們互相嗆聲的場景。想法閃進腦袋的瞬間,覺得荒唐;但隨著舞碼持續推演,配上編舞家劉奕伶於會後座談的分享,漸漸搞清楚那份既視感到底從何而來。


從舞者經驗出發,表現「競合」微妙心理
若用一句話概括,《Game On》是「為舞蹈人而生的作品」,以「競爭」和「較量」為主題,重現了科班出身的舞者毫不陌生的場景——不斷排練、不停競賽,次次與熟悉的人,亦敵亦友的微妙關係悄然發酵。就算不學舞,你我生活中總有過競爭,也能從舞蹈編排、舞者互動、道具安排中看見似曾相識的情景。

較量之前/生命共同體
《Game On》由5位舞者共演,開場時他們是夥伴,一同排練,只要有人失誤就得從頭來過,彷彿生命共同體。隨著不停重練,耐心消磨、笑容淡去,摩擦逐漸產生;但小情緒無妨,出了排練場便消散,真正的考驗還在後頭。


與他人較量/競爭的複雜心緒湧現
練習是為了磨練技藝,磨練是為了沒有破綻、接近完美,完美是自我追求、也是賽場上的最佳武器。來到舞作中段,「競爭」逐漸開展,舞者們互相拉扯、推擠、爭執,每一次肢體碰上地面的重響,都為競爭現場再澆上熱油,求勝的、憤怒的、自責的火燒得越來越旺。他們爭什麼?首席、出賽代表、成功的可能⋯⋯這是象徵表層的慾望;而成就感、害怕失敗的心緒、擔心自己沒天份的心魔⋯⋯或許才是內裏盤根錯節的思緒。

「參賽者」在競爭過程中被定義、被抉擇、被決定離去或留下,半推半就地更深入了解自己與對手。不過微妙的是,舞者們不只是對手,下了場更是同學、朋友,或必須合作完成演出的夥伴。這樣的「競合」關係,微妙而難解——因合作而互相欣賞或不滿,也因競爭而彼此爭鬥或相惜。

與自己較量/崩潰邊緣的自我傷害
各種情緒在內心碰撞,崩潰感漸漸襲來。《Game On》也把這樣的激烈碰撞舞了出來,成為全作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橋段——舞者們不停重複一樣的動作,有人跳躍旋轉、有人極致伸展扭曲身體⋯⋯力度從小到大,最後每個人都耗盡力氣。劉奕伶將這段取名為「自殘」,呼應著追求目標的途中,身心不可避免的不適感。面對低谷,每個人各有紓解的辦法,而在《Game On》當中,舞者將其演繹得微妙,「一開始蠻唯美的,怎麼後來越來越不對勁⋯⋯」劉奕伶打趣說道。


結合現實狀態與表演性,是《Game On》最大挑戰
為了重現「競合」狀態的矛盾心理,劉奕伶與舞者花了非常多時間回憶過去,回想地方舞蹈班的學習經歷、幾乎不會流動的同學與對手、無數次的舞蹈比賽⋯⋯藉此找回彼時面對矛盾人際關係的心態,讓表演更為生動。這對劉奕伶本人來說,並不是陌生的課題,她從小習舞,跳進北藝大、再跳入紐約美國比爾提瓊斯舞團(Bill T. Jones/Arnie Zane Company)擔任專職舞者,舞蹈生涯歷經大大小小的比賽,最終回到台灣用心做舞蹈教育。

這段舞者互相自我揭露的過程,也延伸出《Game On》最具挑戰性的細節,「要怎麼把現實狀態用表演的方式自然傳達,像是舞者要同時在舞台拿出最好的一面,又要用自然的小表情演出平常互動、或比賽輸了的狀態⋯⋯」劉奕伶解釋。全作細節花了很多心思堆砌,藏在現代舞與傳統戲曲身段交融的姿態裡,也埋在舞作與古典鋼琴配樂《帕格尼尼主題狂想曲》和《藍色狂想曲》的互動當中。

現代舞與火爆實境秀
所以說,看現代舞表演怎麼會想到火爆的廚師競賽秀?追《地獄廚房》時,時常想為何廚師們常因雞毛蒜皮的小事就情緒潰堤?為什麼這麼容易耐心失守,瘋狂抱怨同事?這些存在我心中不怎麼重要的疑惑,卻意外從《Game On》找到解答——因為「競合」而生的微妙心理,在「高壓」環境下不停被催化,終將爆發。身為局外人的我們,平時難以參透舞台/螢幕前後的難處,而《Game On》就像一座藝術橋樑,為觀眾搬演了融入表演張力的部分現實。

從藝術看見與生活連接的可能
還記得當晚《Game On》演畢,正思考著將平時予人高冷印象的現代舞作,連結接地氣的實境秀,真的妥當嗎?正好有人向劉奕伶提問:「希望別人怎麼理解你的作品?」她思量後回答,「我當然在意自己的作品,能不能讓觀眾讀到什麼,但那是我的課題。」因此在創作《Game On》這支敘說舞者故事的作品時,她不停假想、猜測、實驗如何讓擁有不同生命經驗的人讀懂作品,最後她說,「不會將想法強壓在觀者身上,只要可以從作品中聯想到什麼,跟自己的生活做連結就好了。」這或許呼應了Camping Asia藝術計畫「Open for all」的理念,讓藝術面向大眾、彼此理解,從表演藝術中看見與生活串接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