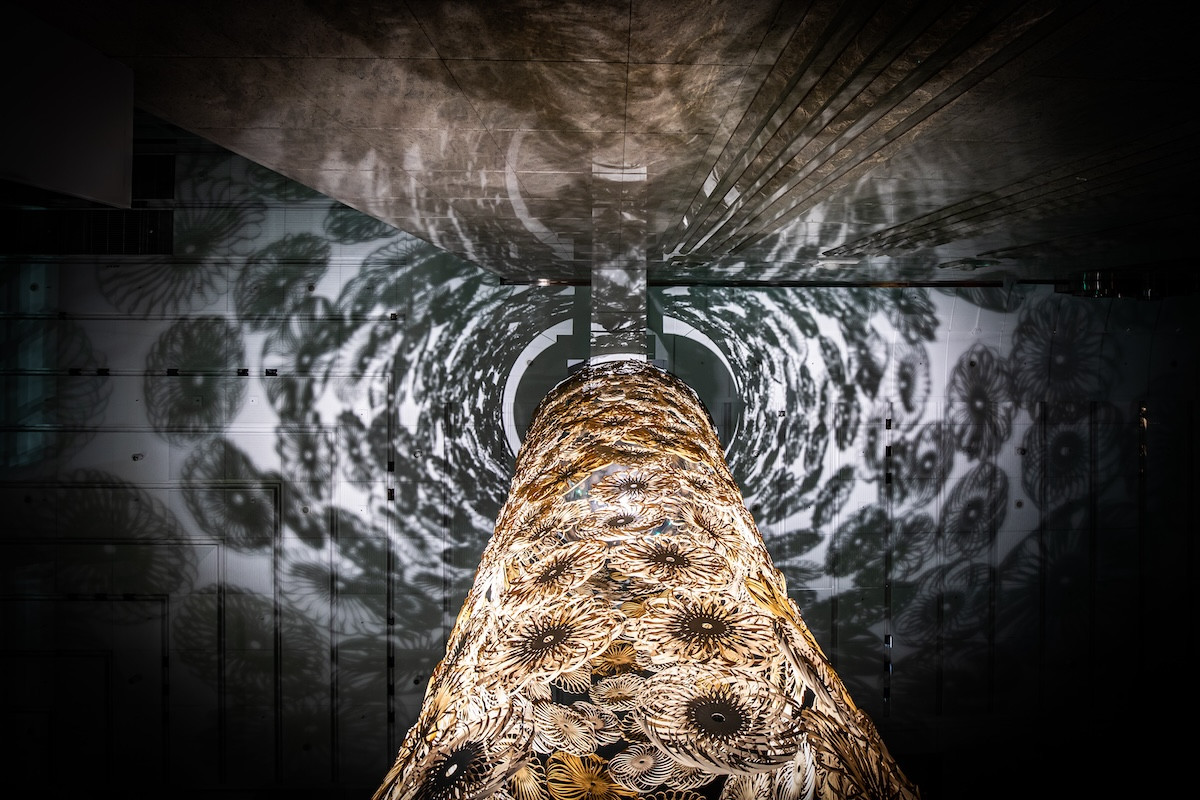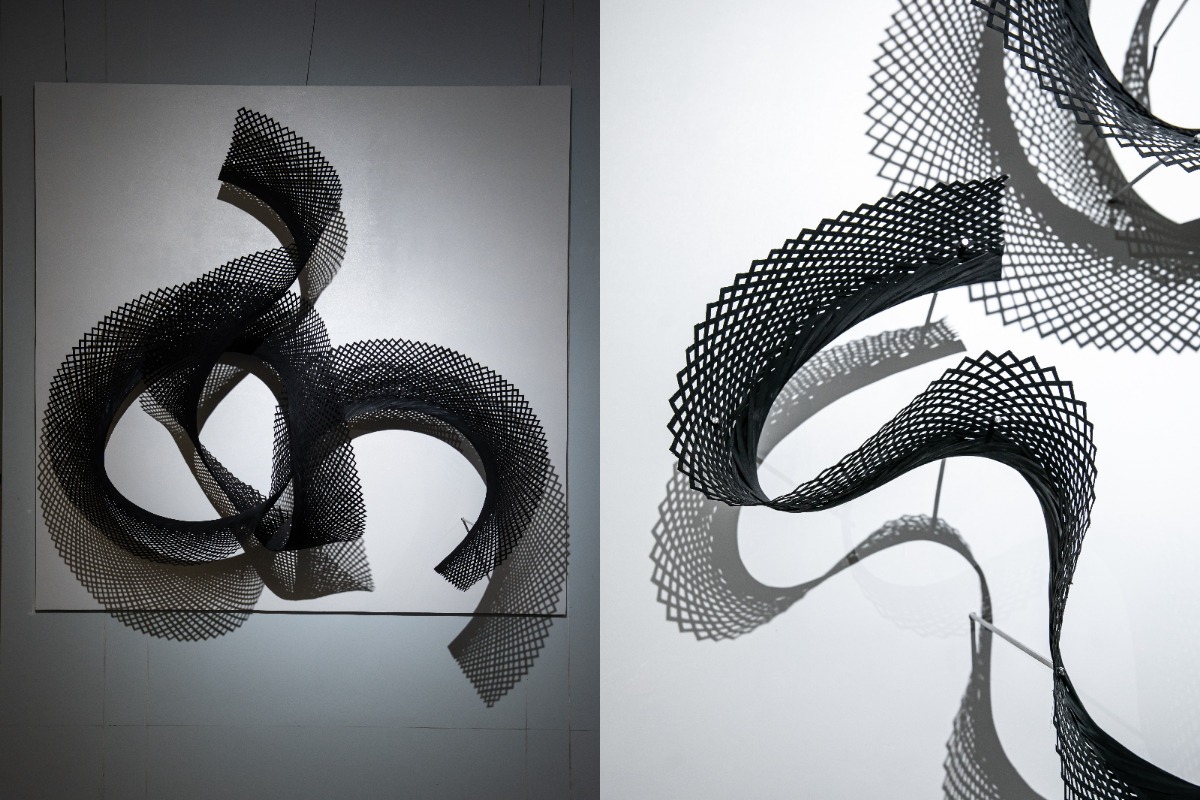從十六歲開始投入玻璃創作工藝的許鈞淵,作品充滿自然寫實的風格,已是各大藝術展館典藏作品的重量級藝術家,並於2022年獲得由聯合國教科文認列的IATOPL職能技藝全球國際認證玻璃大師級證書。走過數十載,他仍保有一顆赤子之心,醉心於每日與火為伍創作的日子。
談起當初為什麼投入玻璃工藝,許鈞淵回溯兒時,自小便生長在玻璃產業蓬勃的新竹,姐夫也從事玻璃製品產業,「我從小就耳濡目染,看了也想跟著學。」許鈞淵說自己學得很快,師兄們學習這門工藝要花八年,他只學了一年半。秉持著創作熱忱投入玻璃工藝多年,以藝術創作為主,量產為輔,也協助許多設計科系學生製作研發產品。
「應該算是有遺傳吧。」許鈞淵認為自己的藝術天份可能源自媽媽,「我媽從事服裝產業,我們去百貨公司看亞曼尼的西裝,我回家只要把圖畫出來,她就會依照版型加入自己的創意元素,然後完整重現出來。」過目不忘的影像高敏銳度,也展現在許鈞淵自然寫實的玻璃創作風格。
信手捻來的創作靈感
「玻璃很好玩,想到什麼就可以做出什麼。」他的創作靈感和題材隨性,卻專注呈現細節。曾經有次看完侏羅紀恐龍特別買書研讀,觀察每種恐龍的身形,然後透過空心玻璃吹製打造出一座恐龍公園。吹製空心玻璃的難度很高,必須快、狠、準,精確拿捏燒熔玻璃的溫度,並於三秒內快速塑形,尤其腕龍脖子細長,一定要一次到位,才能完整呈現脖子的流暢弧度。而此系列擬真詮釋恐龍造型,目前有21件由新竹市文化局典藏。
許鈞淵的創作多取材於大自然。作品中《印第安的故鄉》玻璃花器是他到南美旅行看見野雁南飛延伸而來的作品,同時結合了兩種玻璃技法。空心吹製的瓶器造型猶如黃昏時分的高聳山脈,稜角分明,雲霧繚繞,靈巧的野雁凌空飛躍山間,以實心塑形的雁鳥色澤清澈栩栩如生,充滿了畫面感,善用玻璃將自然意象轉譯為藝術收藏,是他的強項。

自然寫實的動物姿態
許鈞淵分享他為豬年製作的《生肖雙層玻璃存錢筒》,存錢筒內部為實心塑形的小豬,透明外層則是空心吹製而成的大豬,摒除以往圓滾滾的卡通形象,他強調的是展現動物肌肉的寫實比例,比如背部下凹的曲線、圓垂飽滿的肚子、柔和的下巴線條,以及耳朵、四肢等線條皆真實地詮釋生物象徵。
這件作品必須先捏塑實心玻璃小豬,然後吹製空心大豬的局部身體,放入小豬之後,用剩餘空心身體部位封起來,最後再黏上四肢,點綴細節便完成,完全看不到接縫的精湛技術,讓人多次端詳,饒富趣味。同時,亦有牛、馬、狗等生肖動物系列存錢筒,可投入88個1元銅板,充滿吉祥意味,讓許多藏家爭相收藏。
《海中精靈》是多年前許鈞淵代表屏東琉璃工作坊出賽電視節目而做,因比賽主題定為夏天,他第一個聯想到就是海洋,還有鯨豚追逐船隻躍跳於海平面的畫面,然後透過地理頻道觀察海豚游泳姿態,仔細研究牠們拍打水面前進的動作,運用空心吹製玻璃予以重現。這件作品共有十隻至十二隻海豚,逐一做好之後再行組裝,透明鰭尾均略帶粉紫色,靈動討喜的姿態,也讓他順利於比賽中勝出。
拿出這套作品的時候,發現有局部玻璃破裂,為了讓攝影師能夠順利取景拍攝,許鈞淵現場便熟練地拿起火槍快速進行修復。首先預熱玻璃破損處,將其燒軟之後,用金屬夾鉗修飾掉,又是一件完美的作品。每天與火為伍創作的日子讓許鈞淵感到開心,「我跟火很有緣耶!我也是義消。」完全無懼高溫火焰。
而採訪當日,也巧遇銘傳大學商業設計系學生前來請許鈞淵協助製作設計作品,他看著學生繪製的比例圖,走到一旁翻找適合的金屬腳架,拿起準備好的空心玻璃管原料,便開始以火槍燒熔玻璃管,玻璃管逐漸膨脹,到了適當溫度離開火源進行吹氣,吹製力度和次數全然拿捏於多年經驗,他一邊拿尺規量測大小,再行數次吹製,直到玻璃變薄隨高溫斷開,便完成圖面上的高腳杯,整體過程不過三分鐘。


混搭多元材質的創作
試問為什麼選擇空心吹製為主要創作技法?喜於挑戰自己的許鈞淵說:「空心吹製比較難學,但是學會之後製作實心玻璃就沒問題了。」為了挑戰自己的玻璃技術,以呈現到最細,許鈞淵選用鈉玻璃以實心塑形技法製作無數隻黑色玻璃螞蟻,擬真度極高,連纖細的步足都能一一真實呈現,結合他從海邊撿來的木頭,遠看真宛如螞蟻來回穿梭於木頭紋路之間,而近距離定睛觀賞,會發現每隻螞蟻的造型與姿態都有些不同,有些細小前腳抱著白色米粒,有些互相交頭接耳傳遞訊息,結合木頭與玻璃展現自然生態一景。

工藝必須具備功能性
許鈞淵的後期作品型態獨特且都具功能性,好奇他如何思考功能性?卻被反問「你知道為什麼會讓它有一點功能嗎?」原來是因爲他之前參加工藝大賽,以「維京戰艦」為題,採用空心吹製技法打造了一艘透明戰艦,輕薄的船身嘗試吹製八次才完成,象徵勝利的旗幟好似飄揚於海上那般生動,他為了忠實演繹更買書來研讀划槳、盾牌等細節。好不容易入圍了,卻沒有得獎,追究原因才知道是因為作品不具備功能性而影響討論結果,「藝術品要有功能性,我第一次聽到。」讓他心裡受到很大的衝擊,從此以後,改變他思考作品的方式。
在他的認知裡,工藝是一種跟生活相關的藝術。除了創作之外,許鈞淵也接量產訂單。比如他為臺南咖啡店設計製造的《心型杯》,由上往下俯瞰,杯緣是完整愛心,透明高腳杯連結著吸管一體成型,以空心吹製技法製作了兩百餘件。早期他也根據業主需求訂製商品,比如當時流行海洋文化便須設計七至八百種樣品提供參考下單,曾經一款玻璃水鳥油燈的美國外銷量最高紀錄可達上億件。所以有實用性這件事情,在後期創作也成為必然考量。

根據族群消費力定價
在思考作品型態和銷售價格時,他會依據客群收入而定。「假設我想賣給年薪五十萬的族群,我會設計該族群消費得起的藝術品。」他以月薪五萬的上班族群為例,「這個區間的消費者大概會買三百塊以內的商品。」藉此反向推理,將商品價格除以三或四,即是工廠定價,再往下推斷成本可能只剩五十元,他就會設計這個價格的作品進行販售。同理也適用於百萬年薪或更高收入的企業主,而此套邏輯便是來自他個人長年與廠商通路合作的經驗。
那麼臺灣普遍可以接受玻璃工藝品的價格範圍是多少?他舉例以前在臺中當街頭藝人的經驗,「那一次我做玻璃玫瑰花,剛開始一支賣五百,大家都拿起來看就放回去,我索性改成一支一千,結果當天賣了幾十支,我覺得人好奇怪,怎麼會有這麼奇葩的事情。」他苦笑著摸不著頭緒。
曾經歷外銷蓬勃時期,他有感臺灣玻璃市場深受中國抄襲的影響而萎縮,藝術收藏族群亦愈來愈少。他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臺灣消費者普遍購買藝術品都是送人,而不是自用,「剛畢業出社會的新鮮人月薪大多三萬,扣掉房租、交通費、娛樂交際費用,要存到錢很難」因此縱使臺灣的玻璃製品已經賣得比國外便宜,仍然不容易成為大眾頻繁購買的選擇。
但是他依然看好臺灣市場的潛力,政府亦有推動產業跨界合作的補助,近期他甫完成一件鬱金香擴香的專案,未來也將會持續創作直到八十歲,不斷挑戰自己,呈現更多美好的玻璃工藝。

文字/何芳慈
攝影/一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