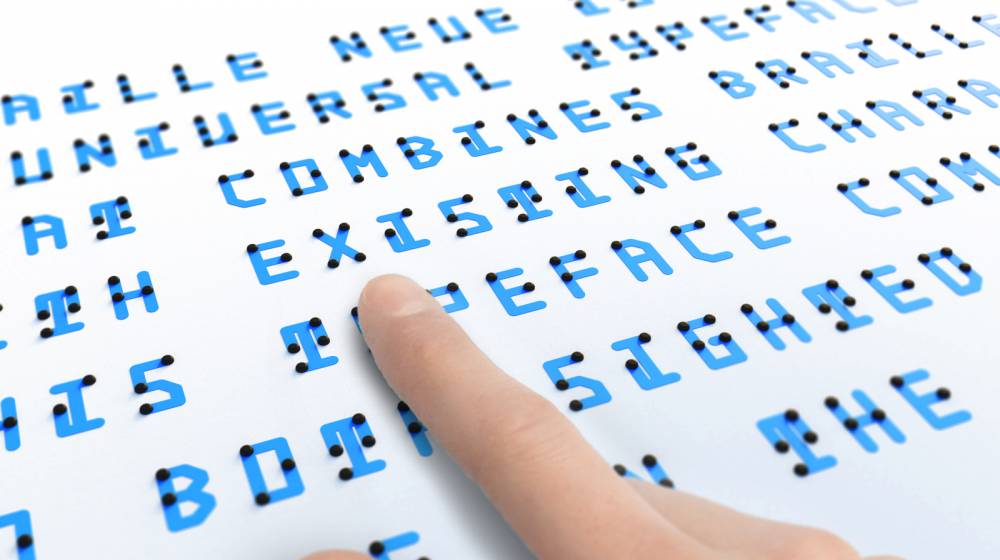上週去參加今年關渡雙年展的開幕。由於每次關渡美術館的開幕都喜歡辦在傍晚,所以搭捷運時已屆黃昏,但天色雖晚卻還有光暈流轉,車窗外的房子、車子,都抹上了一層美麗的玫瑰色。越往淡水駛去,景物就逐漸安靜下來,天空也變得低了一些。
我很喜歡從關渡捷運站一直走上山的過程。那是一段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路,用力走大概也要花個二十至三十分鐘,才能到達半山腰的美術館。一開始走石頭路、上樓梯,然後站在紅綠燈前望著對面的加油站,左右都是蓄勢待發的汽機車,然後再開始爬坡。不知道是誰想出的點子,坡上每隔一小段就會有一個立牌,上面印了我念不出標題的詩句。當已經開始有點喘氣,覺得脊椎微微發熱時,就會到台北藝術大學的門口。那時才恍然大悟:原來才走一半啊。但轉進校園,繼續沿著坡道上行,左手邊就會出現可愛的乳牛吃草,右手邊半個台北的景色則逐漸顯露。
我在一間應該是剛開沒有多久的小木屋買了晚餐,然後走進美術館。平常冷清的展館只有在開幕時會特別熱鬧,策展人、藝術家、媒體、親友團都在裡面轉來轉去,忙著招呼、開玩笑、籌備等各式各樣的事情。我順著樓梯走到二樓挑高的大廳,觀賞其中一位藝術家教導大家自製鈔票的影片,正狐疑為什麼看不到開幕的舞台,就發現人潮一直往旁邊咖啡廳對外的通道走去。據主辦單位表示,之前每次開展當日都天氣不佳,今天難得天晴氣爽,還有微風相伴,於是大家興高采烈地跑到外面的露天陽台辦開幕。我坐在最後一排的角落,看著前面的表演者愉悅地演奏出曼妙旋律,而遠處矗立的101則在淡淡的雲霧中特顯雅致,彩霞的顏色慢慢變化,就像大夥的心情一樣是暖色系。
這一次因為文創專題採訪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總監、亦為現任畫廊協會秘書長林怡華小姐的時候,她提到藝術其實是一個非常小眾的事情,從來沒有誰跟誰是競爭,藝術的產業只要好,每一個人都會好,所以她並不擔心Art Basel來到香港會瓜分台北藝博的藏家(詳情請見La Vie十月號的封面故事)。因為來自官方的補助有限,也非每一個展覽、每一場表演都能夠獲得企業足夠的支持,要在競爭激烈的業界中生存是很殘酷的;但藝術家們並不需要彼此紅了眼,互相計較資源分配不均,而應一如近幾年盛行的各種「連線」,跨區域、跨國、甚至跨各大洲,去找到一個更冷靜而貼近社會現實的觀點,以及生存方式。
我有一個作劇場的朋友曾對我說,在北藝大舉辦藝術節的時候,學生們裝扮地花枝招展、歡鑼喜鼓,她卻很害怕這整個過程都是一種自high──旁邊的人根本無法體會他們想要表達什麼,也不知道要怎麼認識他們。藝術真的很小眾,雖然現在許多藝文單位及媒體(La Vie也是)總強調將藝術帶入生活,但更多人難免覺得作品太「難懂」,畫廊太「高級」,美術館又太「拘謹」。看著這一群群在開幕時彼此嬉鬧的年輕藝術家們,我在想他們即將(或正在)面對的台灣藝術界是什麼樣子,他們心中有什麼樣的計劃,他們會擔心來看展的是否都只有圈內人嗎?
就像傍晚的天空絕美,但一下子就入夜了。我離開關渡美術館的時候,四周昏暗,黑色的校狗趴在對面美術系館的石頭椅上,百般聊賴地看著我。即便如此,身後如皇宮一樣透著金色光芒的關渡美術館,卻還有許許多多的人正熱絡。他們是台灣藝術界重要的一角,未來也還要面對各種考驗,像黑夜一樣又長又重的現實壓力、經濟壓力、各方雜音都會持續干擾每一位創作者。究竟怎麼樣走過這些,走向黎明,或許惟有親身經歷的人才能知曉了。
希望台灣的藝術界如那天關渡的天空一般,長久都能透著溫暖的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