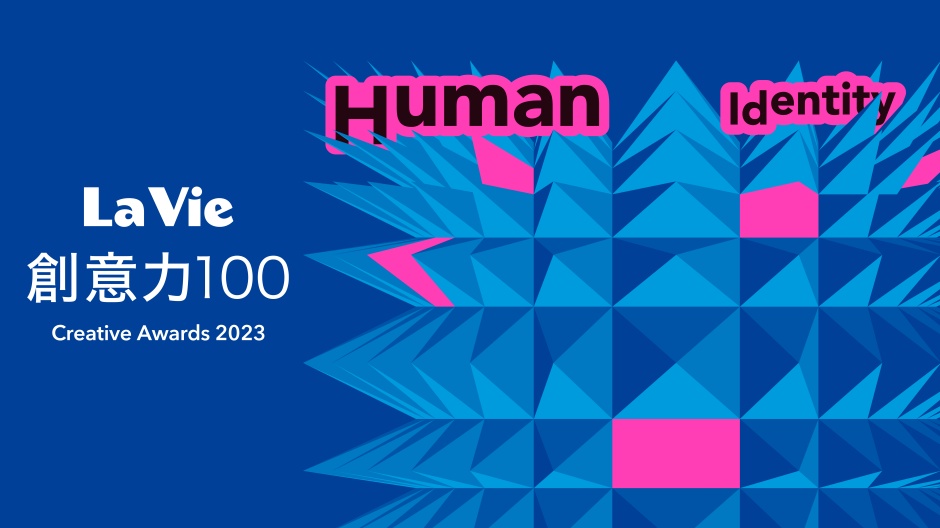文學改編,一直以來都是國際間影視作品重要的創作文本來源,無論是《哈利波特》、《少年Pi 的奇幻漂流》、《派特的幸福劇本》等青少年或流行小說,或經典文學《大亨小傳》、《悲慘世界》都可看出文學小說與影像的密切關係。
相對來說,近年來台灣文學改編電影或影像作品就較為少見,去年度台灣電影票房前三十名當中,也僅有《等一個人咖啡》改編自輕文學作品,不見其他改編自經典小說或觸及歷史時代背景的文學。也因此,以「向台灣作家致敬」為概念籌拍的《閱讀時光》短片計畫更顯得特別,由甫獲得國家文藝獎的王小棣導演策劃推動,一口氣邀請鄭有傑、沈可尚、廖士涵等七位台灣導演,拍攝包括文學前輩楊逵《送報伕》、朱天文《世紀末的華麗》、駱以軍《降生十二星座》等經典小說作品,為台灣文學與影像創作的結合開啟了新的契機。
文學與電影,共享一段閱讀時光
「我自己非常喜歡看小說!以前大家都常問導演:哪個導演影響你最多?我第一次遇到這問題後就開始想,總覺得影響我最多的其實是小說和作家。」王小棣導演如此聊起籌拍《閱讀時光》的初衷。台灣優秀的小說作品甚多,僅僅能挑出十部題材作為拍攝主題,即使是對於平日就熱愛閱讀小說的王小棣來說也是件很大的工程,「那時我和製作人黃黎明像考聯考一樣跑遍圖書館,翻遍台灣小說惡補。」
王小棣除了與黃黎明兩人親自海選書單外,更邀請《中國時報‧開卷》前主編的李金蓮,以及台大台文所特聘教授梅家玲加入,「我們的前提共識是,以兼及台灣各個歷史年代和多元社會面向為方向找書。」接下來三方各自草擬了一份書單,讓人意外地三份書單加起來不過20多部左右,在十分聚焦的狀態下進行討論挑選出最後十部作品。
「其實有不少很棒的小說因為執行性的困難,像張大春的《公寓導遊》,我們非常想拍,甚至也都給大春打電話,他都一口答應『好!沒問題』,但因為找不到那個時代的公寓大場景,怕會犧牲掉小說的原貌,也只能先擱置。」在王小棣心目中,台灣文學小說就像是個激發拍片靈感的寶庫,想拍攝的好小說總是讓他惦惦念念。
文學╳電影的交織與加乘
「當小說家的文字已經如此完美、完整時,導演是很難超越的。」導演鄭有傑聊起他拍攝〈老海人洛馬比克〉時的心情,對於自大學時期就十分喜愛夏曼‧藍波安小說的他來說,拍攝過程中不免對作家的意見十分在意,「一直到在蘭嶼開拍的某一天,夏曼‧藍波安大概感覺到我的忐忑,主動跟我說:『你就拍吧,忘掉原作者,這就是你的創作,就盡其在我,不要擔心!』」這句話讓鄭有傑彷彿吃下定心丸,不僅細膩地再現小說中的情感與海洋文化,也將導演自己對蘭嶼的觀察融入影片,成為一部交織著小說家與導演心思的動人作品。
「前陣子和作家們聊天,他們還開玩笑說:『為什麼作家都不太喜歡作品被改拍成電影?如果改得不好,那不就把我們作品給毀了!但如果導演改得太好,那還要我這作家幹嘛?』」王小棣笑著談起這次牽起導演與作家合作契機的過程,「所以,我們在和作家溝通取得同意時,第一個爭取的就是導演詮釋作品的空間。很感謝的是,我們都很順利得到作家們的信任,或者說是一種超越個人喜好的善意!」換言之,電影導演對文學改編的創作自由度,是在一個相互信任的基礎上,創造出更為歷久彌堅的影像經驗,讓普遍收看電視與網路的觀__眾,能因為影像的衝擊與感動,回流到紙本閱讀的原初觸動,於是無論是觀眾、導演或作家,都可以因為這段時光而在文學再度相聚。
循著純粹的閱讀感動而拍
「做這次計畫,我最大的感動在於『純粹』。」身為《閱讀時光》系列的主要推手,王小棣娓娓聊著他的感想,「如果這個計畫是要改編成一部完整電影,很難避開市場、觀眾和預算考慮,但因為是現在短片的形式,我們幾乎可以感覺到每位導演對小說及作家的『忠心耿耿』。」
拍攝文壇前輩楊逵《送報伕》的導演鄭文堂,就是王小棣口中「忠心耿耿」的導演之一。對早期參與過社會運動的鄭文堂來說,楊逵的文學從很早對他的人生志向有很大的影響,鄭文堂也曾表示自己是「帶著楊逵的影響走進了電影圈」,因此,拍攝過程中,若說鄭文堂是懷著想重現最初備受感動的心情,一點也不為過。
對於拍攝駱以軍《降生十二星座》的導演廖士涵來說也是如此。這部連在王小棣口中都被稱為「真是夠難拍了!」的小說,被譽為是駱以軍的經典成名代表作,蒙太奇式拼貼書寫風格串聯起跨時空的多線故事,而小說中重要的意象主線「快打旋風二代」電玩,則像是密碼般連結起導演廖士涵的成長經驗(或說是台灣五六年級生的共同回憶),「拍這部片讓我想起大學時最喜歡的導演大衛芬奇(David Fincher),於是決定用比較實驗性的拍攝手法,和攝影師一起激盪出後投影、空間虛實交錯的鏡頭。」這些是在廖士涵過往作品中少見的嘗試,卻也展現出一位導演得以專注於影像創作時,所激發出的「純粹」爆發力。
體會故事,建立在地的情感
《閱讀時光》系列中,王小棣親自執導了〈行走的樹〉,作家季季以自己的婚姻為主軸,回看1960年代白色恐怖陰影下的前夫楊蔚涉及告密、作家陳映真被捕等文壇往事。書寫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作品甚多,且當議題多半圍繞著政治犯是否為受害者做討論時,王小棣卻挑選了關於政治犯受到扭曲的人格,也讓他們的家屬受到壓迫的小說題材。這樣的角度在當代試圖帶出什麼樣的意涵呢?
「我想是一種歷史的承擔。」王小棣指出,現在當大家提到白色恐怖時,往往指稱誰是罪人、誰是受害者等等,「但是當我每次在讀季季《行走的樹》的時候,都還是感覺到一種很大的氣度,季季說『因為知道他發生過那些事情,所以我會原諒他。』我覺得如果可以用心體會這種狀態,不只是想著誰是罪人、誰要道歉、要有個交代,這些當然不可或缺,但是我們理解歷史的同時,也應該要能走出更好的未來。」
在十部影片剛完成時,工作人員辦了場長達5小時的放映會,作家及導演們一口氣如馬拉松般看完所有短片,「這樣連著看下來,還真的是有滿多讓人激動的感動,這個你成長的地方,無論是在各種抗爭、政策、環境的改變中,讓你覺得自己很渺小、做不了什麼事。可是因為你生長在這裡,你始終相信說這裡還有別的、台灣不只是這樣。」王小棣溫穩的聲線聊到情緒真摯處,音調稍稍上揚地說道:「但是當那個5小時的放映後,你就知道那個你相信的東西是真的在的!可能是在家裡書架上的小說裡、可能是在沉默的人的心裡,它們是真的存在的。會讓我有種對在地的感情,原來我們生長的地方是這麼的豐富。」
藉由影視與文學,重新看見歷史
點開《閱讀時光》官網,若稍加留意可以發現在每部影片名稱後,加註著幾行灰色小字,提綱契領地提示著影像中對應的社會背景。楊逵的《送報伕》對應出「1895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日本」後的基層人民困境、朱天文的《世紀末的華麗》描寫「1987年:解除戒嚴」世紀末的台北、而在看似訴說虛擬時空故事的王登鈺的《大象》其實可對讀到「1971年:政府核准興建核一廠」之後台灣邁入的核能時代。
每一部《閱讀時光》系列影片全長不過短短25分鐘,對於要將文學改編戲劇的導演來說已是一大挑戰,但對王小棣來說,他想呈現的不只是台灣文學和影像的共振,「我們想到這十部影片組合起來後,勢必會對應呈現出台灣不同歷史時期的樣貌。」因此特別設計以20分鐘戲劇、加上5分鐘紀錄片的組成模式,在紀錄片中提供關於對照解讀小說描寫的時代、社會氛圍的轉變或小說家本人的心情線索。此外,王小棣也特地邀請熟悉台灣近代史的吳密察教授擔任顧問,就是為了能夠讓影片更詳盡勾勒台灣歷史及社會背景。
共享創作初衷,台灣文學與電影的原創力
針對當前台灣影視產業環境對原創力的限制,王小棣坦言,「導演很容易受外在社會環境、票房考量、或是合作的單位影響,只敢拍既定類型的戲劇,長此以往,甚至導演也會以市場導向侷限自己拍片的內容,可能會想說來加場床戲之類的。」然而《閱讀時光》恰巧提供了導演們打開新的創作體驗,「作家在寫作時相對沒有這麼多外在包袱,比較忠實、深刻或自由的面對內心思維,所以當導演進入到文學世界時,就有機會拋掉心中的雜念。《閱讀時光》就像是讓導演和作家合唱一首聖詩,感覺真的很棒。」也就是在這種去掉商業化利害算計的雜念,單純回到文學場景進行拍片的純粹初衷,才能真正拾回在台灣創作的力量。
投資電影,就是投資文化的發電導體
自從《閱讀時光》播出以來,無論是作家與導演跨界合作的策劃構想,或是深度與精緻度均有一定水準的影像內容,在網友及觀眾間都獲得很不錯的口碑。頗讓人意外地,《閱讀時光》其實是源於文化部的一個標案,由王小棣導演的稻田電影工作室團隊進行籌拍。
王小棣直言,「台灣的政府或民間,長期以來對於做電影或是文創呈現一種弱智的現象。只問會不會賺錢,或是能不能去大陸市場,但大陸充滿了對創作內容的限制。」因此,在近年來政府時常一昧將文化建設與商業利潤畫上等號時,《閱讀時光》的確是個相對難得的標案計畫,也讓人備加期待著重在文化軟實力培育的計畫,是否繼續推行?「我們都很期待這樣的計畫可以持續做下去,但坦白說,聽說這是前文化部長龍應台的意願,我不知道接下來文化部還會不會持續。這項計畫若有變動可能,則將突顯出政府的文化投資還是非常短視近利,對於文化建設缺乏想像力。」
王小棣以日本手工藝品舉例說明,「日本產出優質的手工藝品,之後開始有描寫手工藝品創作的小說,小說改編成電影,電影中又將手工藝品更加乘的表現出來。創作其實是一種導體,它不只是放在電影院、放在書架上,它其實是會放電的!政府或民間投資的時候要知道你投資的是一種導體,要讓它有電、有能量。」
王小棣表示,若《閱讀時光》這類型的案子能夠持續做下去,像這樣文學和影像間相互的刺激,台灣導演的拍片手段可以練得非常銳利,而當作家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改編成好電影,其他的作家看到也會改變想法。影視與文學創作更能夠深入自己的社會、屬於台灣在地的故事也將會越來越精彩。
【完整內容請見《LaVie》2015年05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