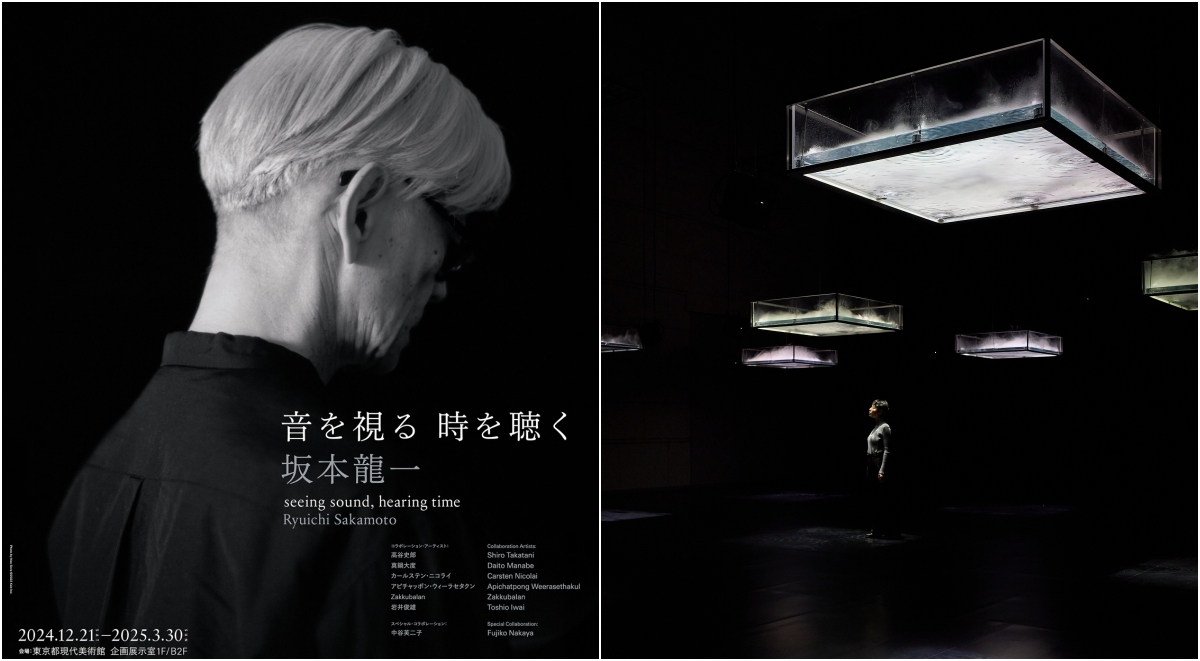「詩人有任性的權利,任性起來有時恐怖有時嬌羞,但幸好我們不是徐珮芬的情人,只是她的讀者,可以任性地讀她,享受她的任性。」
鴻鴻的推薦文,印在黑底方框裡,燙在詩集的背面。讚賞之餘卻直言不諱,彷彿這讀物的作者還在鬧脾氣的階段。翻到正面,灰階封面上是偌大的略為變形的純黑的圓。那輪廓有些像檸檬,擠一下就是流淌的酸。
讀徐珮芬的詩,倒不真的覺得酸。她的詩是黑色的。不是印刷時絕對的四色黑,但終究是無彩度、偏向深黯的那種調性。長期沈入憂鬱之海的身形可說清晰不過,但她倒不放手讓萬物流去,反而如鴻鴻所言,提起精神在自己編織的語言國度中,玩起遊戲來。
「我想買下一條街上所有的
房子,讓你無法再像現實生活
只是微笑經過我」
〈只想和你一起玩大富翁〉
字句不時出現這種幾近少女般撒嬌又霸道的口氣,甚至會從純粹的耍賴變成具毀滅性的威脅。
「我要變成你
最害怕的人
我深信害怕
也是一種愛」
〈我相信害怕也是一種愛〉
幾度無賴後,又瞬間進入聖女的祈禱模式。
「明天都是灰燼
我不會讓時間進來房裏
我不要那些東西弄髒你」
〈陽光燦爛的日子〉
但過份恫嚇和過份虔誠,其實都是一種遠離現實的狀態。小說家何敬堯評之為「孤身旅踏在夢與淚水之間的廢墟,拿靈魂與魔鬼交易,只為了求得『愛』與『被愛』。」
讀完整本,在細緻的文字,大量留白,還有反映作者嘗試逗趣實則支離破碎的拼貼插畫之間,徐珮芬經營出的真實氣氛是「被迫抽離之後的悠長停滯」。這停滯顯然比詩句中的「我」預料得要太長許多。「我」填補不了這麼多的空白,只好不斷反覆生產出囈語般的碎片式對話。
「我被像你一樣的光直接穿透
我被你的光穿透
我被你穿透
找不到地方
可以安睡」
〈光照治療〉
在淘氣、邪惡、不講道理的舞弄背後,提筆人其實倦了,或許眉上都生出幾道皺紋,惟難走的迷宮還不見出口。
徐珮芬在後記中寫著,「比起純粹的死亡,我更畏懼無依之人在頂樓徘徊的模樣。」全書沒有比這更接近現實的描述了。
想像世界是一個同心圓,最核心的是依循社會秩序好好生活的人們,他們或努力,或開心,總之過得非常精彩。越往外形象就越乖離,缺少的東西越來越多,關注的事情益發冷僻,直到最外圍的某一條線,那是臨界點,無法被核心牢牢吸住的人漂浮在這地段,一不小心就會越界。
或許徐珮芬就是曾不小心看過界線後面的景況吧。輕薄的36首詩沒辦法找到回歸中心的路。但最後一首〈我會陪你一起活下去〉中,詩人伴著「我」,想在不完美的現實中走下去,也許能視作契機。
知名的法國概念藝術家蘇菲.卡爾(Sophie Calle),在《極度疼痛》(Douleur exquise)一書中,記錄了她於1985年一場錐心的分手後,向36個陌生人重新敘述分手過程,並請對方分享人生經歷過最痛苦的時刻。整本書乍看之下哀痛滿溢,但若反覆看蘇菲重述那個場景,看她遣詞用字,就能發現她慢慢從激烈旋轉的劇痛中淡出,回到不怎麼樣,卻好像可以依舊過活的每一天。
就算整本都了無歡愉,回頭整理自己的狀態,甚至提筆寫下,對作者和讀者而言都會是一種療癒。故將徐珮芬的詩集視為重生之前的蟄伏,也是另一種看待此作的方法。
「哪一天
我們不再需要語言
就能確定彼此相愛
並且完全
沒有未來」
〈噓〉
沒有未來,「我」卻還活著呢。夢裡也好現實也罷,繼續長出形狀,調出新的顏色。那之後的事,「我們」就不需要都知道了。
text╱歐陽辰柔
via╱啟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