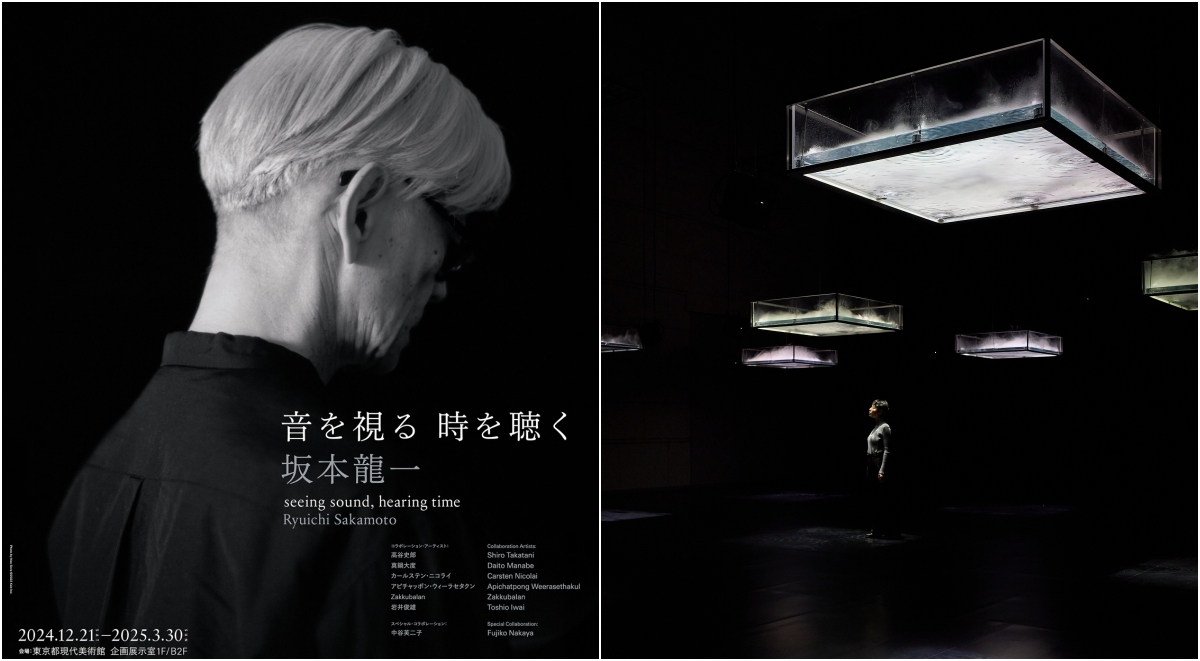認識趙德胤是 2011 年,那時他剛拍完《歸來的人》,正在尋找台灣有沒有人願意發行他的作品。短短五年,他的第四部劇情長片《再見瓦城》——這部 2016 年鋒頭最健的台灣電影——讓他正式登上國際舞台,也是其創作路途上豁然開朗的一個十字路口。從前身為《蓮青》的劇本出發,隨著柯震東、泰國與歐洲團隊的加入,坎城創投的入選,這部跨國合資合製的藝術電影,描述緬甸移工偷渡到曼谷逐夢的愛情故事,是他導演生涯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從第一個鏡頭一直到最後,蔥鬱的色調燃燒著炙熱難耐的氛圍——它不是個可以輕鬆嚥下的電影,但卻值得多次咀嚼。
一杯咖啡的時間,聽著正要 34 歲的他將這部電影描寫的、那難以想像的苦澀緩緩道出,如此雲淡風輕,如此堅定自信,他正要邁開大步繼續多產地拍下去。
爬梳成長記憶,回顧當代社會地圖上的「邊緣」
從《歸來的人》到《再見瓦城》,一路跟隨趙德胤的創作軌跡,城市裡的邊緣人是永恆的主題;這不容易討好大眾的題材,與其僅以電影創作觀看,更像是他整理腦中千縷記憶的片段。16 歲之前在緬甸生活成長,16 歲之後來到台灣讀書,而後趙德胤往返於緬甸與台灣之間,穿梭在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他將所受到衝擊轉變為創作動力,聽見、看見的故事與人物成了創作養分。為什麼要拍?也許出於感性,一種直覺,又或是一種緣分或心理需要。
「在緬甸的長整經驗——不只那十六年,也包含來台灣後再回去的衝擊,這衝擊下有很多正在發生的故事與人物。尤其當這些人跟我聊天,透過交流發現其中很多的故事。對他們來說,他們身在當下並不覺得是戲劇性的發生,就是生活的一些事情;但對我來說卻充滿衝擊,因為我已經是台灣人,我的言行舉止都是台灣人的狀態。《再見瓦城》對他們來說就是我哥哥、姊姊平常聊天的內容,沒什麼好奇怪的;只是當它變成電影後,就會變成一種想像。而這些故事都非常具體,它不再只是腦海裡想到的『一場戲』,完整的起承轉合在他們談話之間、在自己寫的日記中出現。為什麼要拍?因為我就是來自於那裡,又在那裡受到衝擊;若不拍這些東西,要去拍其他題材我也做不到,畢竟這些事物在我的筆記本裡累積很久,沒辦法就這樣跳過。」
流動的城市經驗,造就只存在於腦海與作品裡的家鄉,緬甸
這樣的主題放到全球化軌跡之下來看,也讓趙德胤有不同的觀看城市視角。他坦言不管台北、巴黎、東京,現代化城市在他眼中並無太多差異。「走進一座城市,那些 database 已經建構腦中的城市印象,我很難相信其他新的可能性。每座城市的差異對別人來說可能不同,像某座城市有自己的浪漫,但那些都是表象,我看重的是『人』裡面的『極其情感』。像《再見瓦城》,我甚至不覺得是『移工』,而是『移工』背後的悲劇,這悲劇不管是哪座城市或階級都有可能發生。」曾在歐洲住過很長一段時間,趙德胤卻從未逛過名勝古蹟、美術館或博物館;或許他不太相信那些東西,比較相信自己透過研究人——「透過直覺與所謂的『土方法』,藉歷史、文學、書籍去了解;我看一座城市,可以說我已經有『定見』與『定義』地去走入那個城市。」對照自己生命經驗與生活細節,才能創作出他相信的世界。
唯一與這視角不同的經驗,是 16 歲第一次到台灣的時候。「那時候最單純,對所有人都沒有定義,只對生活很明確:『我要賺錢』。剛到曼谷與台灣時感覺很迷幻,真的有種鄉下人突然走進一個很 fancy 地方的感覺——好像從五十年前突然跳到五十年後的另一個時代。」緬甸作為成長背景的家鄉,對照走過其他全球化城市,讓他的步調與對「家鄉」的訴說,有種現實、魔幻彼此滲透的流動感,如馬奎斯筆下的意象描寫,熟悉、陌生,但保持一段距離的抽離。
真正歸屬的親密感,依然與緬甸纏繞糾結;而與台灣之間的羈絆,對趙德胤來說則是另一種情感面向,「我好像是永遠的異鄉人,『家』永遠只能存在記憶或電影,它不會真實出現在生活裡。」
Mandalay 瓦城,電影從未出現過的城市
《再見瓦城》英文片名為「The Road to Mandalay」,中文有種向後告別的意味,英文卻隱含著向前前去,取名有著矛盾相反的方向感;有趣的是,這座古都、對緬甸人極具象徵意義的存在,卻從未出現在電影畫面裡。「這名字最開始出現是去訪問工人的時候,他們宿舍放的歌就是 Robbie Williams 的《The Road to Mandalay》。這首歌與電影意思完全不同,但依然憂傷、灰色,談的是愛情裡的傷感。」與最大城仰光的英式文化與市景不同,瓦城是緬甸皇帝一千五百年的首都,「它很小、很擠卻最多元。」趙德胤解釋,小時候鄉下孩子都嚮往去瓦城,很多做移工的哥哥姊姊從國外回來都會經過那裡,書信裡寫的都是「什麼時候到瓦城?」這是一座交織移工嚮往、只屬於工人的城市。
「後來英文片名選用『The Road to Mandalay』,還是回到『家』的概念,這些離家的人想要榮耀返鄉。Mandalay 在英文裡除了地名之外,也隱含『shining』、『glory』的意味,用進電影表示往『成功』、『回家』之路的意思,呼應著緬甸移工對瓦城的嚮往;但對故事裡的女孩蓮青來說,她可能是回不去了。」這座畫面從未出現過的城市,轉變成一種烏托邦式的存在,凝聚緬甸移工的集體夢想;趙德胤也在其中偷渡對「家鄉」的糾結——離開家後自己也已成長,人事已非,回不去了。
美學與隱喻
自覺身受西方文學影響頗深,褚威格、杜斯妥也夫斯基、福克納、海明威,孕育趙德胤對戲劇表現方式的選擇。先前作品是在有限資源下完成,像是以偷拍、素人、沒有燈光的方式,種種限制讓他依循台灣新電影的路數:長鏡頭、細節說故事、隱喻運用等等。然而在《再見瓦城》他卻展現出驚人的企圖心,以類似達頓兄弟關注社會議題的手法,用攝影機跟著主角,最後給了一個非常漢內克(Michael Haneke)的結局。
其中有段魔幻卻寫實的戲,趙德胤將蜥蜴變成男性性慾象徵,巧妙做出電影驚人結局前的高潮。這看似超現實的段落對他來說卻是十足寫實,「曼谷很多地方你會看到蜥蜴,這是很常見寫實的,只不過對沒看過的人來說太魔幻,覺得是超現實。現實生活有那麼多事物是關於性的想像;自然地,當下我思考這段時就會試著推向另一個層次」片中看似壓抑矜持的情感表現,其中隱藏許多性暗示,從床上床下的性啟蒙、曖昧、到有意識地在一起,「原本有拍阿國自己發洩的鏡頭,但為了保留結局對愛情的純粹,把柯震東的自慰戲剪掉了。」再到最後的蜥蜴,吳可熙的角色慾望被勾起,這部片的「性」被帶向另一種境界:不只是關於兩個移工的愛情,而是昇華到人類皆會有的慾望層次。
「不同資源下我的美學也會跟著改變。若把美學升為另一層次討論——關於文學、藝術而並非視覺美學,我其實一直受西方影響。西方文學裡談工人憤怒的時候,會去燒東西或砸東西,你能看見他的身體真正在憤怒,用很激烈的方式去表現。」他所建構的世界,是目前台灣還未有創作者嘗試過的另一格局,「若《再見瓦城》再拍好一點,也許美學會有像漢內克《白色緞帶》的感覺,再多一點也許會如柯恩兄弟早期的作品。」融合電影科學技巧,用分鏡訴說故事而非一直客觀觀望,這正是趙德胤有意識去挑戰的。
吳可熙與柯震東
如同李康生之於蔡明亮,趙德胤與吳可熙之間的創作關係也讓人好奇,是否如「繆思」般的概念。他表示一直與吳可熙合作,不僅是因為她是很好的演員,精準度高、表演技巧熟練——「你要她眨眉毛也可以,能夠很細微調整」,事實上趙德胤也沒看過有台灣女演員能像她既職業劇場出身、卻又能素人化的演出。「再來就是我很倔將,若自己合作過的演員別人不用,我會覺得是不用她/他的人有問題——很簡單,我很相信自己的眼光。」演員對他來說是家人朋友,給他們時間,他們會證明自己是很好的演員,而不是大家所認定的「素人」。
對於出乎眾人意料之外的選角柯震東,「對我來說演員是電影創作的工具,若導演有能力與意識,任何演員在鏡頭下都會呈現另一個面向,可以百分之百去掌控。對演員來說他們當然不覺得自己是工具,他們可以自由創造;但他們自由創造的部分是喜怒哀樂、壓抑、憤怒等情緒,而不是要演什麼——要演什麼由我決定,這時由我想像演員就是件很有趣的事,不會是大家心裡認定某些演員只適合某些電影。透過跟他們相處,觀察演員適合什麼——這觀察過程會看到很多大眾不一定認同、或不覺得適合的東西,這也回到《再見瓦城》這次的選角。」趙德胤解釋。也許正因非訓練過,柯震東所有的表演都是很「自然」的。「像是拍哭戲他會哭到沒辦法拍戲,這種『哭』對紀錄片可以,但卻不是電影要的。為了拍一場哭戲,他與我的挑戰都很大,他要嘛哭不出來,要嘛就像小朋友一樣真實地哭——但那不是阿國在哭,是真人的柯震東在哭。」內心還是大男孩的柯震東——「很聰明的大男孩」——正是他最好之處,也是趙德胤選擇他的原因。
未來與再見
最後,談到未來計畫,趙德胤打算更積極地兩者兼顧:國際團隊與資金繼續拍攝劇情長片,但每兩三年拍一次紀錄片,或像《冰毒》的規模,但比《冰毒》更精準。可能會更忙、時間會更少,但對電影也會了解越深,自我要求更高,而這種對美學的追求與討論,也決定他下部電影的走向。關於台灣的故事,他表示目前不急,也急不得。「想拍台灣有幾個方向:一是現在台灣的年輕人,在台灣的年輕人低下階層與上流階層是融合在一起,收入少的人也許過著上流社會的生活,這點對我而言很有趣。另一面向則是歷史,因為台灣某種程度上大家都是移民,對於真正的認同性不具體,而不具體有時就會不夠強悍。但也正因如此,這些組成讓台灣變得非常有趣,東方、西方、家鄉等概念彼此不時衝擊著,整個島嶼跟我自己很像。」從這樣的切入點看台灣,全球化下的台灣之於他是很普世的,顯現的是世界許多地方都存在的問題。
後記:
採訪這天是在金馬獎前的一個午後,當大家熱烈談論著金馬獎,「很實際、很妥善運用時間地去做內容,從不去想這部電影要改變什麼,或去想別人如何看待我的作品,甚至不關心會不會得獎。」趙德胤相當平靜。這並非高傲或置身事外,他只是堅定地維持用電影創作書寫、整理自己的回憶;即便他所寫的是與身在此地的我們如此遙遠而難以想像的困境,也許正因他的雙眼懂得回望,願意正視生命經驗裡的殘酷與悲喜,才能在尋常的愛情故事裡賦予電影血肉,描繪龐大的社會議題格局。穿針引線,邁往家鄉的路,也許在景框裡,他也找尋到了。
Text、Interview / 孫宗瀚、Alice Chan
Photo / Manchi
※本文由Polysh授權刊載,未經同意禁止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