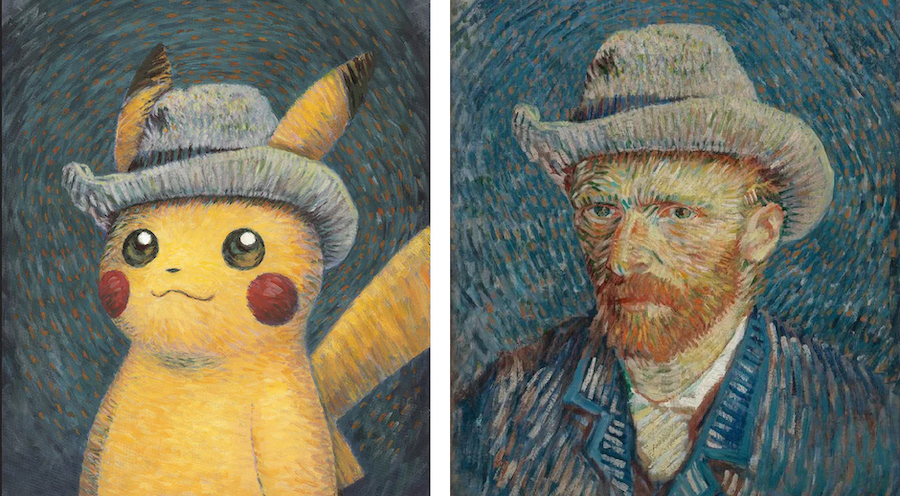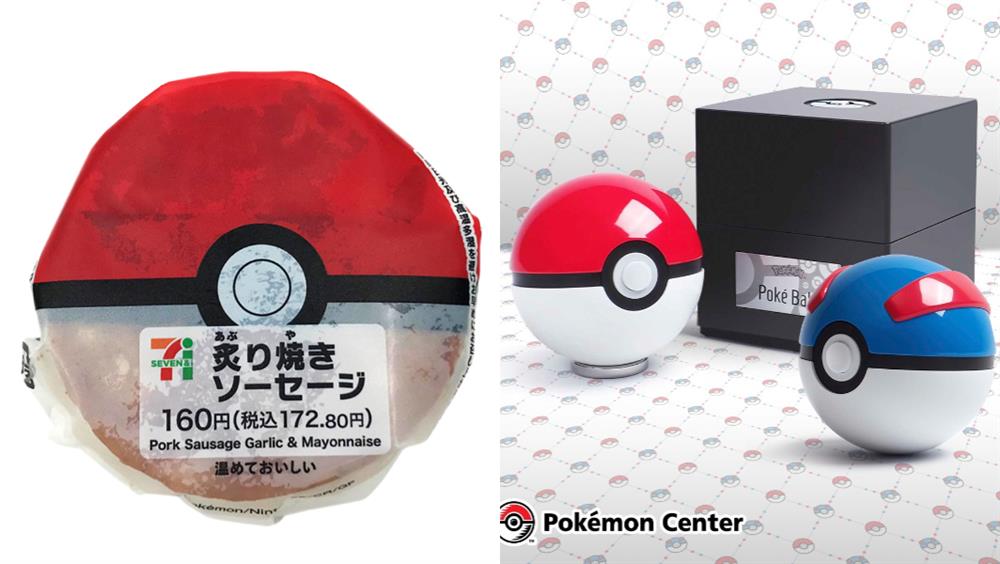每一回重讀由威士忌引誘出來的文字,都是一次重新校對。校對的對象,有時是知識的補充;但更多時候,是給自己倒上一杯同款語境的威士忌,進行氣味的複習與新氣味的探索。比如,在慢慢喝、慢慢寫、慢慢讀的日常,淡淡焦慮著泰斯卡(Talisker)十年威士忌明顯的胡椒辛香,可能來自何處?
說不定與蒸餾廠使用奧勒岡松木製成的發酵槽有關。較長的發酵過程,木製槽產生乳酸菌,帶出多層次的熟果實與風乾水果的風味。我也想過,可能與酒廠取較寬比例的蒸餾液作為酒心有關——這有機會出現較多雜醇的複合之味。也可能因為泰斯卡蒸餾器的特殊向上U型林恩臂(Lyne Arm)所造成的回流(Reflux)有關——特殊的林恩臂造就的蒸餾可變因子,向來都帶有蘇格蘭的北地傳說感。繼續往製程後端推想,泰斯卡威士忌的胡椒辛香風味,會不會也跟酒廠使用傳統的冷凝器蟲桶(Worm Tubs)有關?⋯⋯每當我這樣彈跳追索,這其實是類似文學線性引動的討論,是經由一串接續不可斷的因素共同造成的。
我還沒有找到靠近的解答,目前偏向奧勒岡松木製發酵槽,可能是生出胡椒與其他偽裝成Spices氣味的重要考據。那麼影響更為顯著的橡木桶內熟成期間,這類胡椒辛香風味的討論點又該落在哪裡?這些推想,還有許多值得飲者去靠近。這些靠近,也讓我觸及威士忌文學脈搏的跳動。
這確實是我個人式的一廂情願。重讀威士忌語境,另一層次的校對是:威士忌之於文學的可能對照。試著探究深度,造成威士忌風味可變因素的內在,與我偏執愛上的小說,都存有神諭。兩者在造就的過程中,有技藝,有美學限制,也都透過異質發酵、多次蒸餾、收集回流,萃取出酒體與小說——這兩種從模糊框架中誕生的實體。放寬看,在作品與作品之間,都在看似極小卻有無限詮釋可能的空間裡,面對著無以名狀的認識焦慮。
在我「重讀與校對威士忌及其語境」的同時,我的觸感也在液態中發生。在思流的岸邊,以文字紀錄描繪——這與睡在橡木桶中的威士忌一樣,是看似靜止的一種釀製,以逼近那恍惚卻又浮現的意象。關於泰斯卡的辛香性格討論,多半在蒸餾出新酒之前的製程上,較少聚焦在熟成期間的橡木桶。我也在岸上躊躇,關於「嗅幻覺」這個介於科學又不科學的奇妙辭彙。每每往這個詞彙去解讀威士忌風味,討論有如洄游之魚,死於個人主觀的感官認知。
雖然如此,但這也是single malt如此饒富著趣味、如此引人的地方:一杯一次捕捉抽象的過程。
有朋友聊到這一系列的威士忌文章,對日常飲者與普通讀者來說,都帶有距離感。細細重讀過去幾篇專欄,我無法反駁。溝通日常生活本身,之於我,一直都不是輕鬆的課題。威士忌語境也是一次非主流的局外人嘗試。喝威士忌可以很輕鬆,但嘗試溝通威士忌語境,以及探究威士忌書寫在文字的敘事實驗,不是一件適合笑出聲音的事。
Text/高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