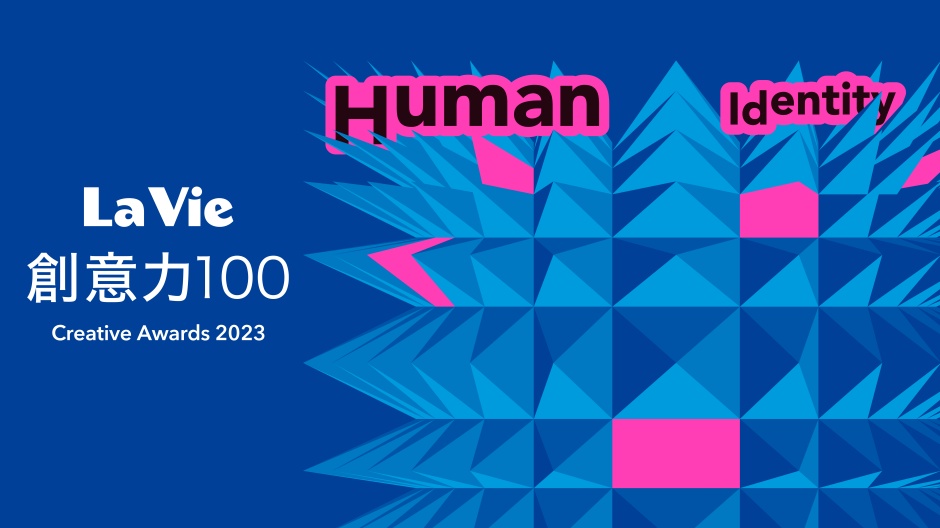文/歐陽辰柔
圖/臺北市立美術館
環繞一圈普里奇歐尼宮(Palazzo delle Prigioni)大廳,泛黃的打卡紙像行軍一樣緊貼牆上。放映機快速重播行為藝術家謝德慶在29跨向30歲的那一年,每日紀錄的大頭照。閃爍的光幕中,他的髮絲從無到雜草蓬生,臉上卻始終沒有表情。
宛如相片中的光線那般昏暗,當時的謝德慶,人生陷入一個無形的桎梏。異鄉生活並不光鮮亮麗,每天醒來都像被灰厚的牆壁屏蔽,沒有變化,也沒有出口。
奔向自由國度的年少歲月
或許對年輕時的自己,會走到那種處境,謝德慶並沒有太多意外。出生於屏東一個傳統大家庭,從小就不屬於升學體制內的勝利組。他從高中輟學,蓄長髮,聽搖滾樂,愛上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卡夫卡,過著近似嬉皮的放縱生活,並從那時開始做藝術。起初是繪畫,後來他用攝影機紀錄自己從15英呎高的二樓跳下,摔碎兩隻腳踝的過程,成為早年創作一個標誌性的舉動。
把身體推向毀滅,乍看令人不解,但那是他在戒嚴時期的台灣,面對極度壓抑的生活氣氛,選擇的「突圍」方式。1974年,他又跳了一次。這次是以偷渡客的身分,從船艙跳進世界藝術的中心紐約,一躍成為了非法移民。
一年,是生命週期循環的長度
缺乏學歷和背景,一個無依無靠的非法入境者,注定只能在邊緣求生存。謝德慶一邊做清潔工作,一邊繼續激烈的實驗行動。例如狂吃中式炒飯直到嘔吐,或請朋友堆上半噸石灰板再並撲倒並壓斷鎖骨。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從沒有創作突破的苦惱中醒悟:這樣毫無意義地耗日子,本身不也是一種藝術?
「早期的創作行動像反面教材,是一個點,讓身體受傷。而後來的作品變成長時間進行,就像一個完整的面了。」他對La Vie表示。
他的「長時間」,指的是一整年。1978年秋天,他在友人的見證下,於布魯克林一座閣樓內的籠子裡,把自己關了一年。過程中不語、不讀、不寫、不接觸任何電視或廣播,完全與外界隔絕。1980年春天,他又以工作室為場景,連續一年每天間隔一小時打卡一次,途中毫無休息日。
這種從短暫激烈的身體性傷害,變為漫長卻帶毀滅性質的創作轉向,和身處底層、每日進行重複工作的生活不免有所關聯;但更多在於內心的衝突。一種對生命概念的根本性質問驅動著他,讓意志力戰勝生理的難耐,徹底重現人類「耗時間」的真貌。「我的作品不關乎如何度過時間,而就是度過時間。」謝德慶說。
1981年,彷彿要從密閉空間徹底解放般,他進行後來被稱為「戶外」的作品。長達一年拒絕進入任何有遮蔽物的空間,每天在曼哈頓下城區十四街以南的地方遊走,把公園當臥室,中國城作廚房,肉品市場視為取暖的火爐,完全翻轉城市的公共性概念,變成私視角的「住所」。1983年,他和另一位女性藝術家琳達用8英呎的繩子綁在一起,一同生活了一年,完成簡稱為「繩子」的第四件「一年行為表演」,逼視無法分割的兩人,如何揭露與接納對方最私密的生活面貌。
掌聲響起時,已轉身下台
照片中一臉青澀的謝德慶,當時並沒有想到,這些執著至近乎瘋狂的創作,往後能奠定他在國際藝壇無可動搖的地位。邁入21世紀,美國重要的美術館陸續整理行為藝術的歷史脈絡,而他因此被推向舞台中央。2009年,MoMA和古根漢美術館分別回顧他最早兩件一年行為作品「籠子」和「打卡」,報導與佳評如潮水般急漲,而他的英文「Tehching Hsieh」,也成為行為藝術史上從此無法抹去的名字。
但對他而言,這些都來得太晚。接在「繩子」後,最後一件「一年行為表演」,簡稱「不做藝術」,內容是一年中完全不看不說藝術,也不走入博物館或畫廊等地。當時他就感覺創作能量的消失。1986年,最後一項行為表演開始,隱世生活了13年後,謝德慶在1999年最後一天宣布「我存活了」,引起極大爭議。然而他心裡明白,「做藝術」已到盡頭。最後兩件消失在大眾眼前的創作,把他緩慢帶回到日常。他放下藝術,拾起一般人的作息,而藝術界在這之後,才驚覺這名男子究竟用生命替觀眾帶來了什麼。
除了服刑,還有喜悅的人生
雖然在那「一跳」後,謝德慶的生活都移往美國,今年卻依舊接受北美館邀請,成為台灣館的代表藝術家,展出「打卡」和「戶外」兩件作品。包括打卡單、遊走曼哈頓時每日於地圖上做的紀錄等文獻資料,一字排開,密密麻麻地鋪滿普里奇歐尼宮的牆壁,就像一頁生命讀本,宏大而沈重。展覽期間,許多藝術界的巨星包括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c)和艾未未都來捧場,瑪麗娜甚至在講座中再一次重申謝德慶是她的英雄。
「即便現在看,謝德慶的創作都還是非常當代。」擔任策展的Adrian Heathfield說。度過、甚至是荒謬耗擲生命這件事,不論何時都發生在人類身上。這是為何謝德慶的創作哲學「生命是終身徒刑,生命是度過時間,生命是自由思考」依舊如雷貫耳。但也如同他不再以創作者自居後,開始認真「做生活」。走過苦澀青春,如今那些晦暗的過往,像溫暖的海浪帶著夕陽餘暉反過來包圍著他。曾經好幾度長達一整年的囚禁,一部份成了名垂青史的紀錄,一部份成為銘刻心中的存活印記。
「作品雖然艱難,但創作本身就是一種回饋。」他笑道,刻著皺紋的臉龐如今滿是豁達,「我還是喜歡活著。光這點看來,就夠正面了吧。」
【完整內容請見《LaVie》2017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