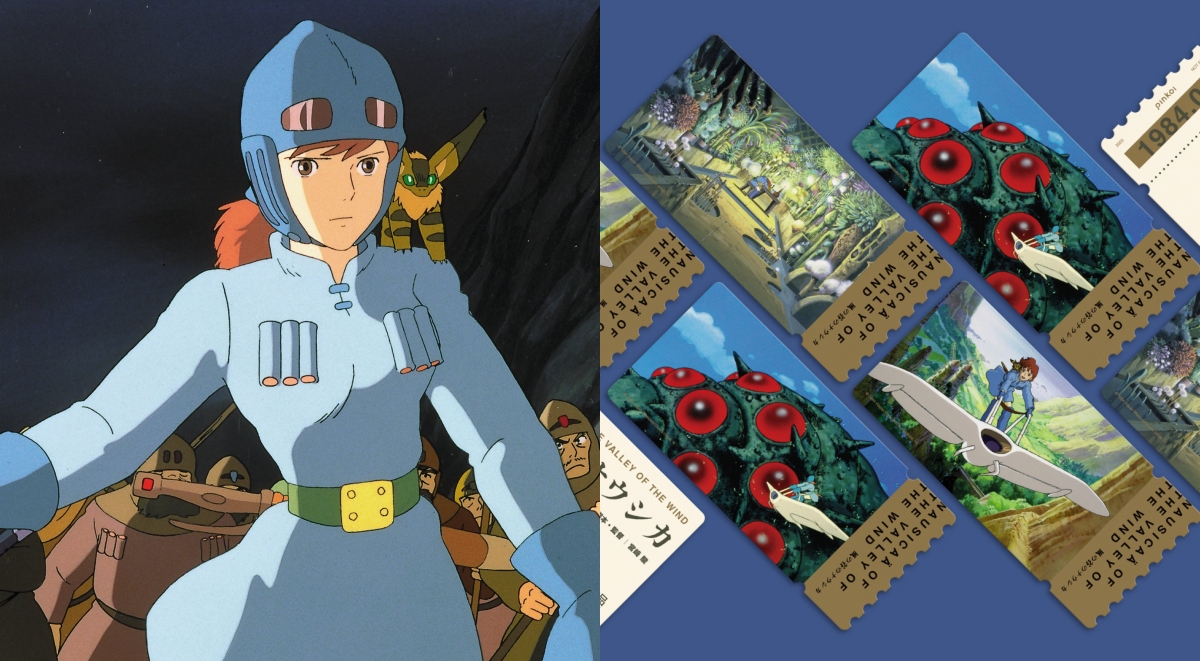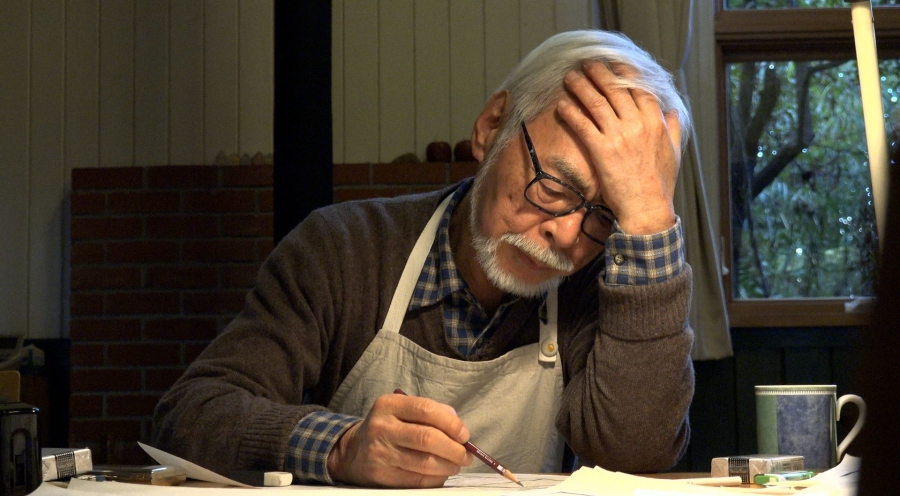從沒想過這一拍,拍了二十年。這麼長的時間足可作一部大歷史的統整追敘,或一段可歌可泣的抗爭紀實。但黃惠偵的鏡頭始終平靜。視線在外頭繞一圈,最後還是回到那個家。
家是什麼?是昏暗老房和牽亡現場,兩點一線的每日來回。十歲時媽媽帶她和妹妹逃離家暴的父親,為了生計,她國小三年級後就離開學校,隨媽媽一起投入陣頭工作,對未來的想像只有「長大後就去歌仔戲班,或當樂師,薪水又好又輕鬆」。日子苦不打緊,但某次長輩隨口直說媽媽「喜歡查某人,是變態」的一句話,卻徹底顛覆她的世界。
單親,牽亡人員,女同志母親,輟學小孩。深具邊緣象徵的詞彙貼滿她的家庭。直到20歲那年楊力州替公視製作影片,前來採訪牽亡現場,她才認識什麼是紀錄片。「這社會看待妳就是不一樣,但他們不認識我,為何可以把我講成就是那個樣子?」恰逢當時攝影機已經相當普及,她開始去社區大學上課,嘗試拍攝自己的家庭,「透過這台小小的機器,可以講講我是誰,擁有自己的詮釋權。」
重拾攝影機,為圓滿一段關係而拍
紀錄就這樣斷斷續續展開。但媽媽在家裡是沈默的。很長一段時間黃惠偵懷疑母親其實不愛她,不然怎會和她無話可說,到外頭卻變一個人,歡顏暢談,結識好幾任女友,甚至花大錢在她們身上?雖然始終住一起,母女猶如各站天秤一端,只能勉強維持平衡。直到黃惠偵自己有了女兒。看著懵懂的女兒一點點長大,她忽然驚覺歲月其實不停流逝,她變老,母親更老,彼此還剩多少時間?
「20歲時,我還在找自己是誰,所以很在意社會給的標籤。可是後來已經知道自己是誰,標籤不再是困擾。即便動機不同,還是想把這部片完成。那對我的意義比較大。」直到此刻,黃惠偵才換上導演視角,準備說一個完整故事。恰逢2012年底多元家庭民法修正草案送進立法院,同志議題再度浮上檯面,她發現這部片的另一層意義:說出她們的日常,分享給更多關心或對同志陌生的大眾。
能說出口的,就不再是問題
從年輕時憎恨母親的冷淡,後來同理為人母的難處,最後反過來展開屬於兩人的對話。開口是最難的,片中經常看見媽媽揮手說「不要再講了」。但黃惠偵認為,就算過去的事情已成定局,只要說出來,都會有改變。最長的一幕,兩人在餐廳各據一方,道出多年前的心結,語畢媽媽離席,攝影機還在錄,而她一人坐在桌邊不停哭泣。「拍這部片改變最大的是我。」她說,「過去我們都各築一道牆,講開來才發現,啊,其實都沒必要。」
為了分別在電視台和戲院播映,黃惠偵剪了54分鐘的《我和我的T媽媽》與89分鐘的《日常對話》兩種版本,前者以牽亡貫串,尚帶點激動的情緒,後者則更完整呈現包括母親、舅父、女友們、妹妹、姪女等家人們的訪問,平實而飽滿。最後一段幼小的女兒撒嬌問黃惠偵的母親愛不愛她,母親回「我嘛愛妳」,像替多年的冷戰劃下句點。電影不但奪下今年柏林影展泰迪熊獎最佳紀錄片,許多觀眾也給予溫暖的回饋,讓母親和家族長輩更正面看待過去不敢言說的同志話題。
「我們」活在同一個時代
雖然講的是私人經歷,卻可能和很多人的生命經驗重疊。黃惠偵過去在勞工協會和中國時報工會工作的歷練告訴她,每個人的遭遇都是大環境的縮影。她的鏡頭接下來要轉向三鶯部落,觀看這一群從鄉下來都市討生活,卻連房子都租不起,最後長期寄居於橋下的原住民。「但不管拍什麼,最後還是回到人本身。我們其實沒有相去太遠,甚至在面臨一樣的問題。所以不管主題是原住民或移工,我都覺得是在拍一個『我們』的故事。」她說。不分文化、階級,人類的情感終究相通,鏡頭內如此,鏡頭外更是。
Info│黃惠偵
曾任職於台灣國際勞工協會,中國時報產業工會,以及台北紀錄片工會暨秘書長。創作主題以社會關懷為主。2016年的作品《日常對話》,獲金馬獎提名,並奪下柏林影展中鎖定LGBT題材的泰迪熊獎之最佳紀錄片。
Text / 歐陽辰柔
圖片提供 / Hui-Chen Huang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La Vie》雜誌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