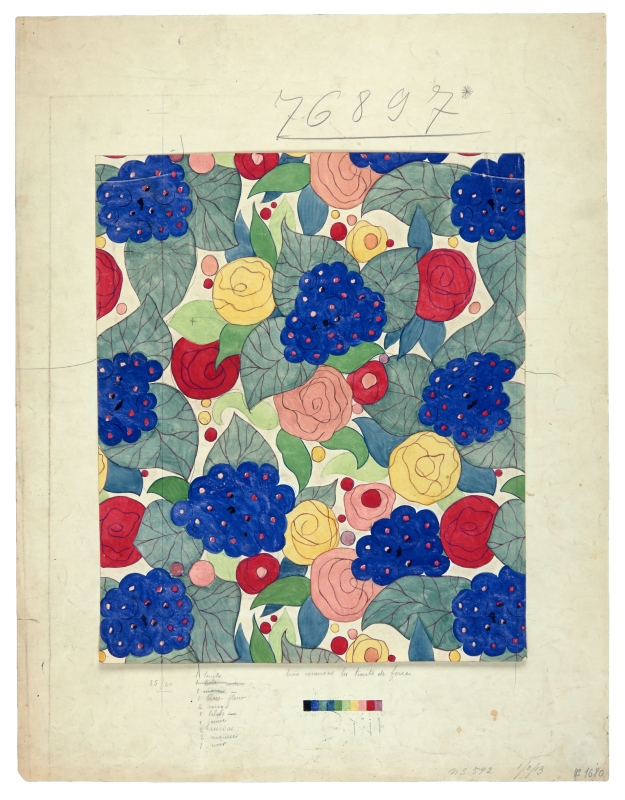不會再有這種時候了。
你觀察螞蟻的足跡,一切如此的新奇、有趣。我們做著單純的白日夢,為喜歡的遊戲盡興。
「我高中的時候,是個航空迷。非常喜歡做模型,那時候沒有現成零件,一切都要用手去磨。用木頭一點一點,做出飛機的形狀。」提到《風起》這部新作,才剛帶領舞團結束國際藝術節巡演的林文中,開場便刺入內心的柔軟,隨著他停頓、緩慢的語調,逐漸勾勒出一個青春正盛的飛行少年。
「我們自己噴漆,飛機外層裹著白色的麻將紙,塗完底漆以後再打磨得很細……做飛機有時候太狂熱,一群人直接睡在學校。學校對面的麵店老闆,帶消夜給我們吃,甚至還陪我們一起熬夜。」回溯那段年代,所有的經驗幾近全新,回憶格外美好。林文中笑著拿出手機裡存著的照片,充滿懷舊感的模糊影像,少年手上的那台飛機,機身彩繪藍得耀眼。
「這段旅程是我人生中很甜美的回憶」——數十多年匆匆流逝,你很難想像際遇帶給人的變化是多麼微妙,當初那名全國科展前三名的數理資優生,跟隨母親的腳步學舞,如今以創作延續自己熱愛的飛行。觀看他與風有關的作品,2015年《空氣動力學》以縝密的動作運算,表現風的現代感。2017年最新作品《風起》,有別於以往編舞風格,這部靈感源自宮崎駿同名動畫電影的舞作,林文中保留更多內在的情感面。
「《風起》是一個關於告別的作品。它告別的方式,就是完全不同於我作品一貫的風格。」
自然界的微觀
國立藝術學院舞蹈系畢業後,林文中旅居美國十年,曾在重量級的比爾提瓊斯舞團擔任職業舞者,2008年回國時他才三十五歲,為什麼要在創作能量豐沛之際,回到舞蹈尚處發展階段的台灣?「我回來的想法很簡單,就好像在非洲賣可口可樂,雖然環境辛苦但挑戰性高。」林文中的作品結構性強烈,理性如同數學,創團作《小》以微型劇場的概念,透過顯微鏡讓視野定格在舞者的肢體,演出後備受迴響,從此延伸出風格各異的「小」系列。脈絡框架底下,他以科學家的精神,不斷實驗與突破,創作中既有現代前衛的面貌,也有傳統的民族元素。
「可能是從小畫素描吧?我常從事物的本質去思考。」解釋自己的「微觀」風格,他想了許久,這麼說。觀察物體的存在,畫下幾何結構,一個接近原型的純粹。「比如《長河》融合東方與現代,沒有套用舞蹈形式,我截取的是東方舞呼吸的方法。」《長河》這部中大型規模的舞蹈,成為2015年台新藝術獎年度五大得獎作品之一,直到今年還獲邀至上海國際藝術節、北京舞蹈雙周等重點劇院巡演。
從河流般的水,至風動的飄移、旋轉,林文中用自然現象建構出身體動態,就像畫家一筆一筆揣摩,刻劃著風景,但到最新的《風起》,一切都改變了。
樹葉掉落,新的便長出來
《風起》講述風與回憶。六十分鐘的意識流裡,林文中以蒙太奇般的拼貼,追溯過去九年的生命經驗。他做《空氣動力學》時看了宮崎駿的動畫電影,「風起,唯有努力生存」——《風起》以電影開頭這段源自法國詩人保羅‧瓦勒里的著名詩句,呈現夢境與記憶交織的浮光掠影。
「宮崎駿做這部電影時說,人的創造力只能維持十年,剛好我從美國回來十年,我發現世界已經不是我想的那個樣子,我開始想,人生真正要的是什麼?什麼是舞台上值得留下來,你願意留下去看一眼的原因?」他探尋問題底層的核心,將這段摸索視作一個旅程,《風起》便是回頭看來時路的終點。
「《空氣動力學》是科學片,《風起》是回憶錄」,林文中說。在《風起》裡,即將枯落的葉子會對樹枝說:「風起的時刻,我們將飛翔」。這種描述有點抽象,他解釋著,風只是一個影子,它讓老舊的樹葉飄落,葉子掉落了,新的會再度長出來。
風吹過安靜的海
人類對飛行擁有無限的想像,電影《英倫情人》(The English Patient)裡,一道孤獨的飛機倒影,帶領我們看見撒哈拉荒漠中的永恆之愛,《遠離非洲》(Out Of Africa)的高潮是主角雙人翱翔天際,一望無際的非洲大草原盡收眼底讓人體會自由的壯闊。
《風起》以飛的意象,揉和瑣碎的虛實夢境。一段海灘的雙人舞,衣袖的飄逸型塑了風的形狀,或者在病床上看窗外的風景……這些段落不約而同地吐露出寂寞。這些是林文中腦海的設想,從舞台極簡的塑料設計,樸素接近米白的服裝、甚至是空間,都停留在一種渾沌不明的中性狀態。
「我想把最後停留在未完成的狀態」,他說。
幕落前的告別時刻, 我們處在安靜中等待回應。還期待甚麼呢?
一個舞蹈家經歷過漫長的創作之路,透過藝術思索生命的意義,也許他什麼都沒聽到,但這無關緊要。重點是當風再次吹起,你依然如同第一次起飛那樣,即使跌跌撞撞,仍用力往天空飛翔。
Info│林文中舞團2017年度製作《風起》
12/02(六)新竹|新竹市文化局演藝廳
12/09(六)-12/10(日)台北|台北市城市舞台
Text/陳韻如
圖片提供/林文中舞團提供
※本文由Qbo藝文頻道授權刊載,未經同意禁止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