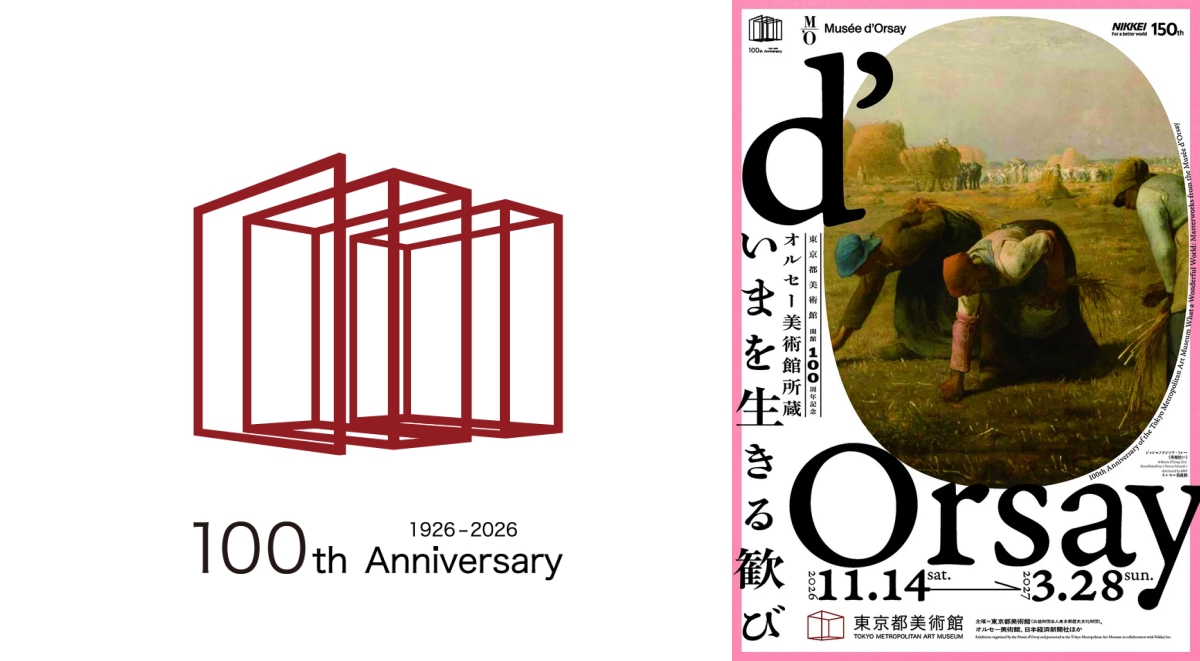在建築產業裡,相信能把建築曲線玩得如此性感與漂亮的大概沒有人能比 Zaha Hadid更具代表性了。她是普利茲克建築獎首位女性得主,更是首位以個人身份獲得英國「皇家金質獎章」(Royal Gold Medal)的建築師,她所寫下的建築王國豐功偉業絕對難以用三言兩語訴盡。
然而這位享譽國際的建築大師,老天卻在2016年3月31日開了個大玩笑,突如其來的驟逝令人錯愕與惋惜。La Vie過去有幸進距離採訪這位曾言「沒有曲線,就沒有未來。」的建築師,與她暢聊關於她對建築的追求,以及人生中所關注的焦點,透過她詳細的闡述,讓我們更加貼近了這位超女力的內心世界。
La Vie(以下簡稱L):哪位設計師或建築師影響了您?您欣賞什麼樣的設計?
Zaha Hadid(以下簡稱Z):從我在倫敦建築聯盟AA唸書時,我就一直對於碎形概念、抽象及爆炸的想法相當感興趣,經由此我們可以解構重複性及大量製造的觀念,我企圖在不同的面向上不斷創造流動性的空間。關於這樣的一個意念,不單單是打破了法則,同時也讓我擺脫了現代主義甚至是之前運動的影響。
回溯到六○到七○年代,當時的人們都極度關心碎形及破解這件事,所有關於藝術的抽象運動都關注著象徵性藝術以及幾何形式的抽象化、以及有關於阿拉伯的書寫方式;我關注於俄國Malevich的書寫方式,他的作品使我得以用抽象的概念,來做為一個研究和創造空間的原則。而康丁司基(Kandinsky)的藝術也是關於這些書寫方式的。我的老師Rem Koolhaas是第一個觀察到這些關係的人,他發現他的阿拉伯學生們,像是我,有那個能力去表達一種曲線的態度,也相信那是關於書法的獨特性,這樣的書寫模式可以在我的平面圖中看到,這也和解構主義與斷裂的空間是有相關的。
二○年代的俄國前衛主義,不但催生出五○年代的都市規劃師的概念,他們當時設計的案子已經運用了後來六○年代烏托邦風行的巨型結構、還有七○年代的高科技風格作為設計的中心思想。Ivan Leonidov 1927年發表的他的畢業設計列寧中心(Lenin Institute of Library Sciences),在形式和科技運用上充滿幻想、不切實際而倍受爭議,但卻超前了建築發展將近五十年。Leonidov在1934所參加的蘇聯工業部的競圖,設計中包含了不同塔樓,一起放置在一個平台上,至今仍舊是都市建築的啟發。Oscar Niemeyer對我有極度深遠的影響,我深信他的原創性、感性空間,還有關於藝術鑑賞的天份,是絕對獨特、無法被超越的。他的作品不但啟發了我、也鼓勵我去追尋自己風格,追求不同尺度的流動性,而我甚至去里約拜訪過他好幾次。
Niemeyer對二十世紀當代建築的重要性舉足輕重,遺憾的是他的天份似乎並未被完充分理解,或許是他眩目的風格常被誤認為過度裝飾,事實上,他對於柯比意(Le Corbusier)在三○、四○到五○年代現代主義後期建築的發展,有一種潛藏的、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力。柯比意確實在三○年代啟發了Niemeyer,但相對的,Niemeyer對於柯比意的影響力亦是再明顯不過的事實,他喚醒了柯比意內心關於雕塑和塑料的想像,並解放了柯比意的燦爛之作──廊香教堂(Ronchamp)。
L:您曾提到在11歲時就決定成為一個建築師,是什麼樣的事情或是人影響了你的決定?
Z:我的父親是一個非常前衛的人,身在那個年代,他對於大都會有著極大的興趣,巴格達是我出生及兒時成長的地方,那個時候正經歷現代主義的影響,包含建築師萊特(Frank Lloyd Wright)和Gio Ponti都正為巴格達設計建築。
就如同許多在開發中的城市一般,有一種對於勇往直前的強烈信念和極度樂觀的態度。回溯到我成長的六○年代,也正是國家建設的時候,當時對建築有極大的重視,這不僅僅在阿拉伯世界,同樣也發生在南美洲及亞洲。就和現在的某些時候類似,城市有一種重生的驕傲。這些年代想法上的改變、解放、還有自由,這些時代的意義對我有極大的影響力。我父親曾被送往倫敦政經學院跟隨Laskian和Fabian學習,全世界各地都正在劇烈地進行社會改革,這樣的意識形態對我而言非常重要,我們家旅行於世界各地,這些事情確實也對我產生了衝擊,教育階段是非常重要的,舉世皆然。
當我還是個小女孩,我每個夏天都會和父母親到歐洲,我的父親都會確定我參觀了每一個博物館、清真寺以及大教堂。我記得七歲的時候參觀了西班牙哥多華清真寺(Cordoba),那是一個令人歎為觀止的空間,當然還有很多很棒的地方,但是這個清真寺在我心裡留下最深的印象。
L:如果你不是一個建築師,你會選擇什麼樣的職業?
Z:當我還小的時候,哥哥建議我應該當第一位伊拉克的女太空人,但我想或許會成為政治家。
L:作為第一個得到普立茲建築獎的女性建築師而言,你的想法是什麼?
Z:贏得普立茲建築獎對我而言是一種肯定,肯定我在20年前預測的未來建築的可能。與其說是身為女性讓我決定非成功不可,不如說我總是很堅決的去努力實現。雖然我現在成功了,但其實經過了很長時間的奮鬥。尤其早期的我是工作狂,不分晝夜,而這是需要極大的專注力和企圖心。不論男性或女性,建築都是個棘手的工作,你永遠會為了想要做出更好的建築而不斷地工作。
L:你提到說你非常努力的工作,那麼人生當中的夢想是什麼?而休閒活動又怎麼安排?
Z:有些人強烈意識到時間的寶貴,一點也不浪費時間。但這個觀點會讓人麻痺。當你嘗試著趕上某個限期的時候,時間不可能為你停下來,雖說工作壓力會讓人創造出好的作品,但是留點時間給你的家人和朋友同樣重要。
L:那麼,在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Z: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將焦點放在如何實現上,與此同時撥點時間給朋友也很重要。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包括了維繫與朋友之間的友誼。
L:就未來的生活形式而言,建築接下來有什麼樣材質與設計手法的躍進?
Z:接下來我還是會大量運用曲線,因為我相信曲線能簡化視覺,這樣一來就能在同一個project中處理更多複雜的結構,視覺卻仍能保持簡潔。至於材料,我們喜歡混凝土,並和工程師一同研發技術為了能發掘混凝土的極限;另外還有纖維混凝土,它的應用將有更多的可能性。混凝土可以是任何形狀,就看鑄模的方法為何。同時間,它有很強的結構性,能夠承受拉應力。強度和可塑性兼具,這就是混凝土無法取代的特性。未來的材料應該是多種特質複合在單一表層上。
舉例來說,複雜的建築表層自己本身就擁有支撐量體的功能,而你可以決定建築表層的感覺以及顏色。它們能延展、扭曲或是纏繞以各種你可以想像得到的方式,甚至可以透明或不透明。我們辦公室成立了一個新部門專責研究與開發一系列專案,在這些案子裡將使用輕量化卻強度極高的材料。
L:近年來,時代雜誌將您評選為百大影響力思想家第一人,而妹島和世則是獲選2010年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的策展人,女性是否真的為這個世代或下個世代帶來風格上的轉變?
Z:建築是一個媒介,我認為能夠透過它解決某些非常重要的社會議題。當代社會並沒有止步不前,而建築必須以新的生活模式參與其中。社會的複雜程度更勝以往,而這必然反映在建築上。在我們的事務所裡沒有任何關於性別的刻板印象,雖然對於女性來說從事建築仍然困難重重,因為依舊存在著某些無法進入的世界,但我不相信建築只有男人能做這樣的刻板印象。建築系一年級的學生有50%是女生,女性不再認為她們不能以建築為志業。
L:對你而言,建築這個行業是否有陳窠?你想打破的是什麼?
Z:我覺得我們應該擺脫亨利福特口中那個量產的建築和城市,創造一個符合當代數位化社會、並擁有多軸心的城市,因為我們的生活早已高度複雜化,以至於建築本身的功能不再單一,建構一座複合式的建築變得非常有趣。
城市分區的方法也需要被轉換,你在這裡工作、在那裡上班、在別的地方娛樂⋯⋯將這些功能整合,在某些區域,我們看待一個城市的方式將會完全被改變。公共建築將是把這些功能聯繫在一起的地方。美術館、戲劇院、藝術中心、游泳池甚至是舞蹈學校,不管是什麼,公共建築對每一個人來說是容易接近的、而且沒有距離的,從上個世紀的城市發展中即開始使用大量的公共建築。設計和建築技術的新突破是讓人非常興奮的。下一步顯然是更多關於材料還有施工方法的探索,透過和工程師的合作,嘗試建立新的材料、並研究人們使用建築更好的方法,我們有能力解決重要的問題並創建一個更有機、更永續的社會。
L:不管是建構中或完工的作品,哪件案子是你感到最滿意的?
Z:位於德國的斐諾科學中心(Phaeno Science Centre)、廣州歌劇院(Guangzhou Opera House)和羅馬MAXXI博物館受到大眾的極度喜愛,主要是因為它們和都市紋理的關聯性都建立得很好。Phaeno剛歡慶了五周年,自它開幕後已有一百五十萬人參觀過,對於一個只有十五萬人口的小型城市而言,這個成果是非常驚人的。羅馬MAXXI博物館在去年夏天開幕以後也廣受好評,光是第一個月就有八萬人次參訪。這個案子最近剛得到英國皇家建築師協會(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的年度大獎Stirling Prize(史特靈獎)以及入圍Mies van der Rohe Award(歐洲建築密斯凡德羅獎)。
自從它開幕之後,地方的居民共襄盛舉、並把博物館當成新的羅馬廣場,這是一件非常值得慶賀的事情,它也成為當地每個人下午或晚上的集會場所,就如同小鄉鎮的廣場一般,它不但是一個博物館,也成為羅馬都市生活的一部份。
可以透過有創新的構築方式傳達建築概念,是非常令人興奮的;相同的例子,廣州歌劇院也是其一,它的主要鋼構是一種全新的結構,叫做spatialfolded plate triangular lattice(空間折板式三向斜交單層網格結構),這種新的結構非常類似單層鋼殼,但它有著非常不同的結構特性,絕對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它完全不對稱、而且複雜,並使用了古老的施工方式、並結合了新科技。為了確保結構的穩固性,它包含將近59個鋼的結合點,沒有一個是一樣的,而且是砂鑄的,然後用雷射光及GPS定位系統精準地組合在一起。
L:對你而言,在設計家具與建築上的思維有何不同?
Z:產品設計對我們來說很重要,因為和建案相比,產品設計可以更前衛、且更快被執行出來,同時也激發我們的創意。這些跨界的合作提供了很棒的機會,讓我們用不同的尺度、不同的載體去表達我們的思維。我們將產品設計的過程也視為是設計研究的一部分,它包含了兩個部分:將我們的建築研究應用在產品設計上,但我們也從產品設計的過程中得到回貴。當然,藝術、產品設計和建築在設計原則上有著共通之處,這是合作的概念,從彼此互相探索間得到成長的力量。重點在新領域找到關鍵的合作對象,並促使創新的概念成為主流。
L:在世界各地待過,是否有最喜歡的都市?
Z:我必須說我很享受伊斯坦堡的複雜與多變,你永遠不知道在下個路口會遇到什麼樣的驚喜。這些偉大的城市,有著自己的韻律和能量,彷彿是個有生命、會延伸的有機體,我總覺得可以從其中學習到許多東西與感受到它的能量。在城市裡,都需要一些空間讓它延伸和收縮,但我認為需要放手去創造某些東西,才能讓這些偉大的城市進行這種有機的生長。
L:你是否會與其他建築師分享或討論自己設計的案子?
Z:在事務所當中當然會與建築師討論,而事務所之外卻不會,除了與自己的朋友討論想法,因為我不喜歡一直討論自己的案子。
L:你還想替誰做設計?
Z:設計日常生活物件是相當有趣的一件事情,而這些概念的發想通常也反映了社會的種種型態,不過產品的設計往往和完成品相去不遠,建築則非如此。我對於能將建築結合社會議題深感興趣,為醫院以及住宅做設計將會是很有啟發的。
L:你是否偏好流線型的設計?而有人將你的建築歸為數位建築?
Z:其實我所考慮的是怎樣把一個概念與具體的幾何圖形,以全新的方式去呈現,不論是城市與景觀的流動方式、空間全新的動線、車流方式、人的行動路線。這是一個無間斷、連續的線,像是無接縫的一個接一個。而所謂的數位建築,其實我屬於數位化之前的設計,我會從平面入手並且操作設計,因此通常我會將概念用繪圖的方式呈現出來,最後才是運用許多平面圖與數位科技來解決三維的東西。
文|廖淑鳳
攝影|Steve Double
圖片提供|Zaha Hadid Archit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