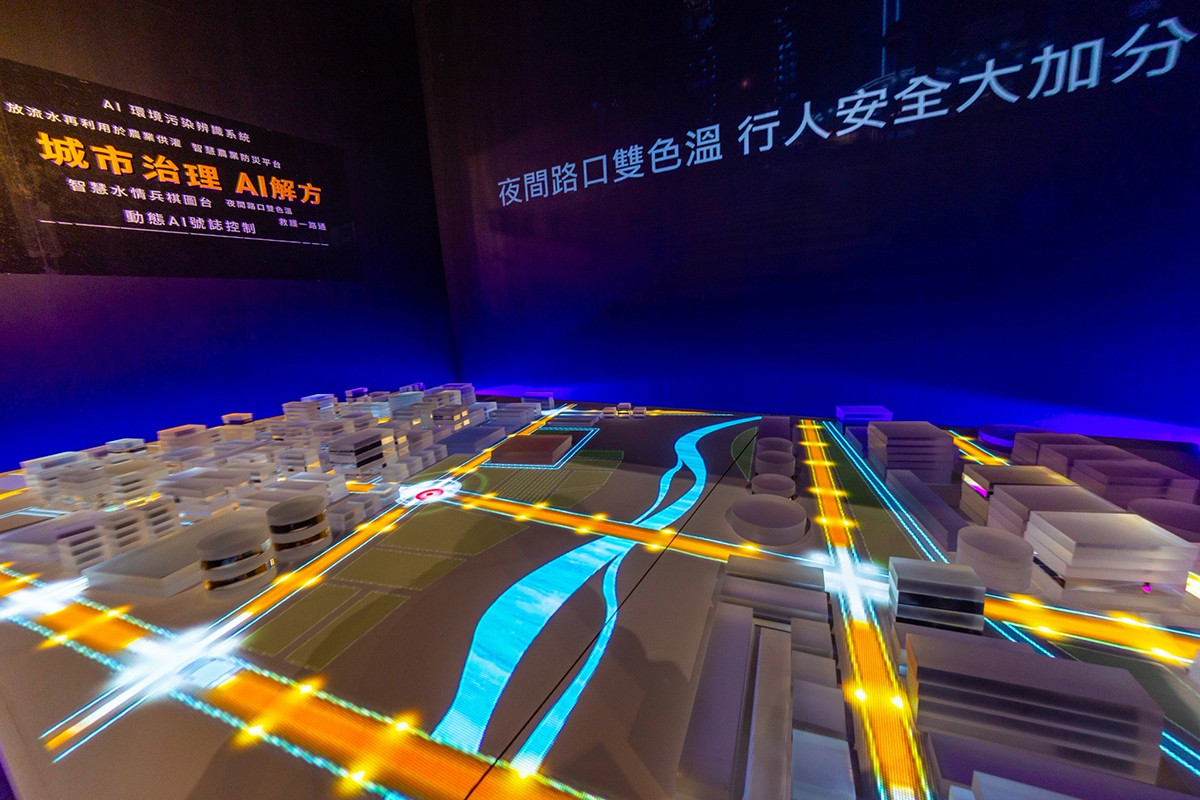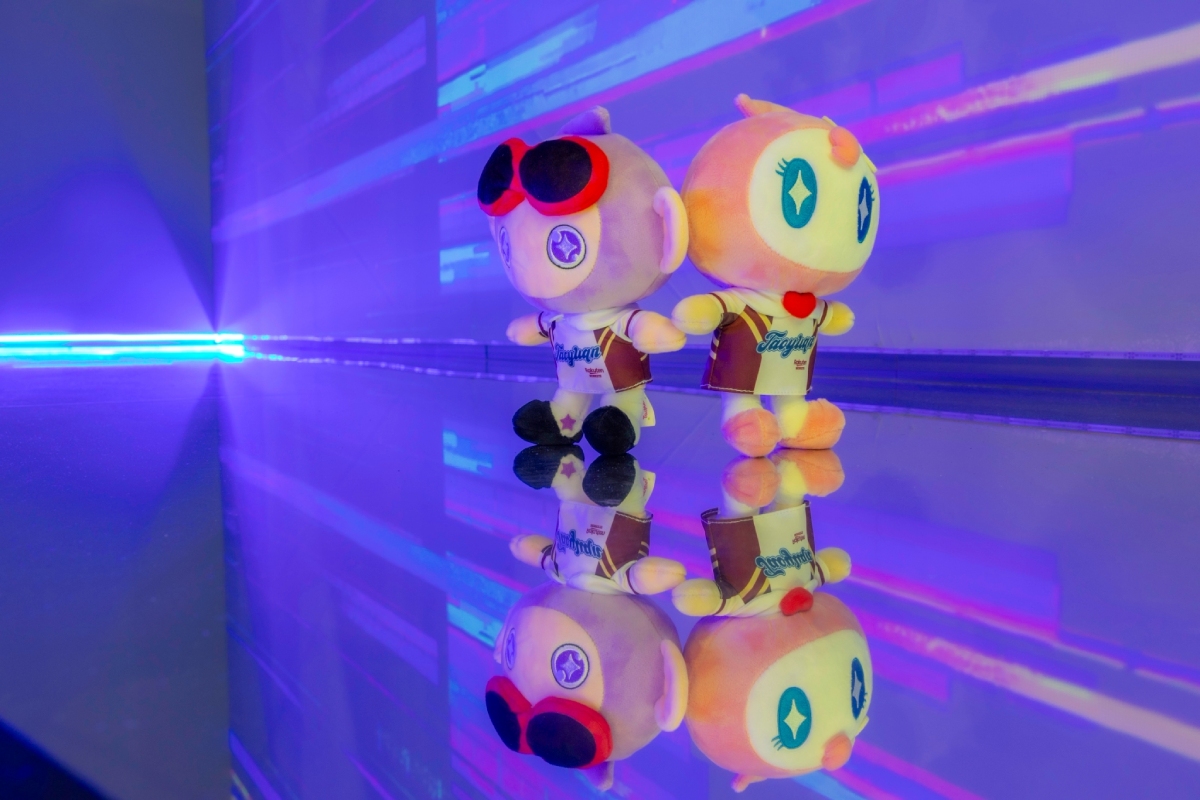本文選自La Vie雜誌2020/8月號《島嶼的想像》
大家都說太陽下山,夏曼‧藍波安(達悟語:Syaman Rapongan) 看到的是太陽下海;大家說的星星,是他族語中的「天空的眼睛」。他在《八代灣的神話》寫傳說故事、《冷海情深》面對重返家鄉的複雜情感,《老海人》則深入漂泊的海上靈魂,蘭嶼的海洋與自然,是他筆下不變的世界觀。
不論你來自哪裡,都會對你出生、成長的地方有一些童年記憶,這個記憶會主宰著每一個人成長過後的、不變的,對那座島嶼、那座城市、那個部落,有著很好很美麗的記憶。我的故事來自蘭嶼這座島嶼,島上的家族有起有落,我的家族是航海家族,我們很喜歡說故事。我的古典文學就是家族的傳說故事,從我的祖父開始跟我講起,他讓我愛上這座島嶼,他讓我認識了海洋、讓我認識了月亮跟潮汐的關係,他讓我從神話故事認識這個民族所謂的混沌時期。這些故事完全有別於希臘羅馬神話,我們也有自己的創世紀神話,我們也有造物、海洋之神,或是仙女的故事。

現在很多在台灣寫作的人的作品,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城市星巴克咖啡的作品,你沒有風的感情、沒有雲的浪漫、沒有陽光的酷熱,因為你都在冷氣房;你感受不到颱風的魅力、颱風的好處,你看不到凶滔駭浪的壯觀,也看不到厚厚的雲層在山的那一頭的恐怖,因為你都在高樓大廈。而這些大自然所有的元素,構成了我小說裡非常重要的核心,用這個東西,變成一種對大眾既疏離、又貼切的世界。很多讀者會看不懂我的小說,你雖然天天看月亮,但你沒有下海,你不會知道月亮跟潮汐的親密關係在哪裡?台灣很多孩子會去游泳,但什麼叫漲潮什麼叫退潮?他們完全沒有概念。而這些都是我的小說世界,風、雲、雨、太陽、海浪、傳說故事。
由體感建構的海洋世界觀
很多人出生在燈光明亮的醫院,但我出生在黑暗的家屋,我躺在茅草上。我來到世界聽到的第一個聲音,是媽媽、爸爸、祖父母和我說話,從第一句語言,開始發展我的聽覺,當我開始用眼睛看,我有了視覺。我還很小的時候,媽媽就會抱我到涼亭,跟我講故事,等到我會走路了,就會跟姊姊一起到海邊。海洋會把流汗的身體洗淨,海上變成我們的冷氣房,我自然而然學會游泳,會游泳後就會睜開眼睛,看模糊的魚。我們平常都睡在涼亭,爸爸去獵鬼頭刀的時候,所有部落的孩子就直接睡在灘頭。小時候沒有電,黑夜對我們來說是非常美的,一抬頭就看到的「星星」,在達悟族語裡沒有這個字,我們說那是「天空的眼睛」。一聽到浪的聲音,就知道現在是風平浪靜還是波濤洶湧,大自然就是這樣孕育我們的敏感度。

海的顏色在陸地上是湛藍的,可是湛藍是一種視覺美學,當然你從自然科學來說,那是經過太陽光折射。但我們是用體感認識大海,用身體去感受海,游到外海深處的時候,會有一種神祕的恐懼。到外海100次、1,000次,就會對環境熟悉,就會自然進入到我們講的很邪門的內化,那是大自然的靈氣,是黑色的美。全蘭嶼的人都知道關於月亮和潮汐的知識,上弦月是初一到十五,之後從下方慢慢消失,島上的男人就是靠這些海洋知識維生。潛水抓魚不要在退潮,退潮魚跑得很遠,因為魚也要去找食物吃啊。漲潮退潮的變化,可以帶來很多不同的物種,很多很多。

大家都知道人類有男性、女性,動物也有公有母,但我們的魚還要分類,有女人魚、男人魚,是指給女性、男性吃的魚,還有老人魚、孕婦魚。女人魚有公也有母,可是牠是美麗的,我們說女人吃的魚叫「真正的魚」。男人吃的魚也是有公有母,可是男人魚在我們族語叫作「不漂亮的魚」。這就是我們民族的美德,用美麗的魚來描寫女性,男人尊重女性,所以達悟的社會不是父權社會,我們是雙系的。月圓的時候我們去抓魚,魚的油脂會比較美麗,油脂很好,那是孕婦吃的魚。老人吃的魚腸子會臭臭的,這些魚可能是雜食或到處覓食,但我們要吃的是牠的內臟。
這就是蘭嶼人的海洋觀,你不用教蘭嶼人怎麼區分女人魚、男人魚,我們一看就知道,這是我們的基因。女性吃的魚是美麗的魚、彩色的魚、優雅的魚,這是我們對女性的愛,對祖母、媽媽的敬愛,對太太、女兒的尊重。就像島上的人稱呼彼此一定會附帶孩子或孫子的名字,說她是孩子的媽媽、孫子的祖母,不管男性女性都一樣,不會直接喊名字,因為我們要尊重他們是有孩子的人。
習慣背後都是很深的信仰
生命中有兩個影響我最深的人,一個是我姊姊的外祖父,我跟我姊姊是同父不同母,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已經瞎了,可是他確實是造船的好手、抓魚的好手,他定義男孩子就是在山裡筏木、海裡抓魚,這就是他定義男人的價值。還有一位是我祖父最小的弟弟,他是紅皮膚的孩子,傳說中他是被詛咒的嬰孩,一直活到我高中他才往生。他們的勞動力、他們的哲學一直影響著我,把身體帶到海上、把身體帶到森林、把身體帶到田裡。他們說要會做自己的船,你才叫作這個島嶼的男人。

海裡面有很多大魚,你不一定要傷害牠,這是我們的信仰。我們不會去射超過自己能力的魚,因為你的魚槍會被帶走,在能力可以掌握之內去抓一般的魚就好。捕到大魚會跟周圍的人說捕到小魚,要去捉魚也不會跟人家說我要去哪裡,因為魔鬼會聽到你的話,這些習慣背後都有很深的信仰。上禮拜另外一個部落的姪兒去打了一條受傷的浪人鯵,我就問他,你幹嘛去抓受傷的魚?後來我聽他講,那條魚也很難受了,也可能會死掉。可是從我的觀念來說,不去傷害已經受傷的人,也不傷害已經受傷的敵人,你要傷害是要在對等、健康的關係,他是我的仇人,也不能趁他生病的時候打他,更何況是動物。從蘭嶼人的觀念來說,人有人瑞,魚也有魚瑞。《白鯨記》裡的白鯨就是魚瑞,我不可否認那是非常好的小說,可是我的問題是,為什麼一定要殺白鯨?如果是我,我不會殺,我會對牠說,我看到你了,你走吧!一條鯨魚要活到那麼大,憑什麼用人類科技的力量、用野蠻去結束一個非常美麗的動物?我要問的是,為什麼?

記得國小的時候在學校看到一張世界地圖,太平洋被切了一半,我也不懂為什麼要把海切掉。2005年我前往南太平洋的庫克群島,在拉洛東加島的小書店找到以太平洋為中心的地圖,我很激動,我終於找到它了。這張地圖現在就掛在我的書房,我跟很多漢人朋友說這個故事,太平洋被切一半,很多人都無感。但我們是海洋民族,我們對於海,會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情感,那是你們很難想像的愛。
夏曼‧藍波安
1957年生,蘭嶼達悟族人,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淡江大學法文系畢業。文學作家、人類學者,島嶼民族科學工作坊的負責人。1992年出版第一本書《八代灣的神話》獲中研院史語所母語創作獎。《冷海情深》獲1997年聯合報讀書人年度十大好書、《老海人》獲2010年金鼎獎。另著有《黑色的翅膀》、《海浪的記憶》、《天空的眼睛》、《大海浮夢》、《大海之眼》等。
採訪整理|張以潔
攝影|張藝霖、劉松
完整內容以及欲知更多島嶼敘事,請見La Vie2020年8月號《島嶼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