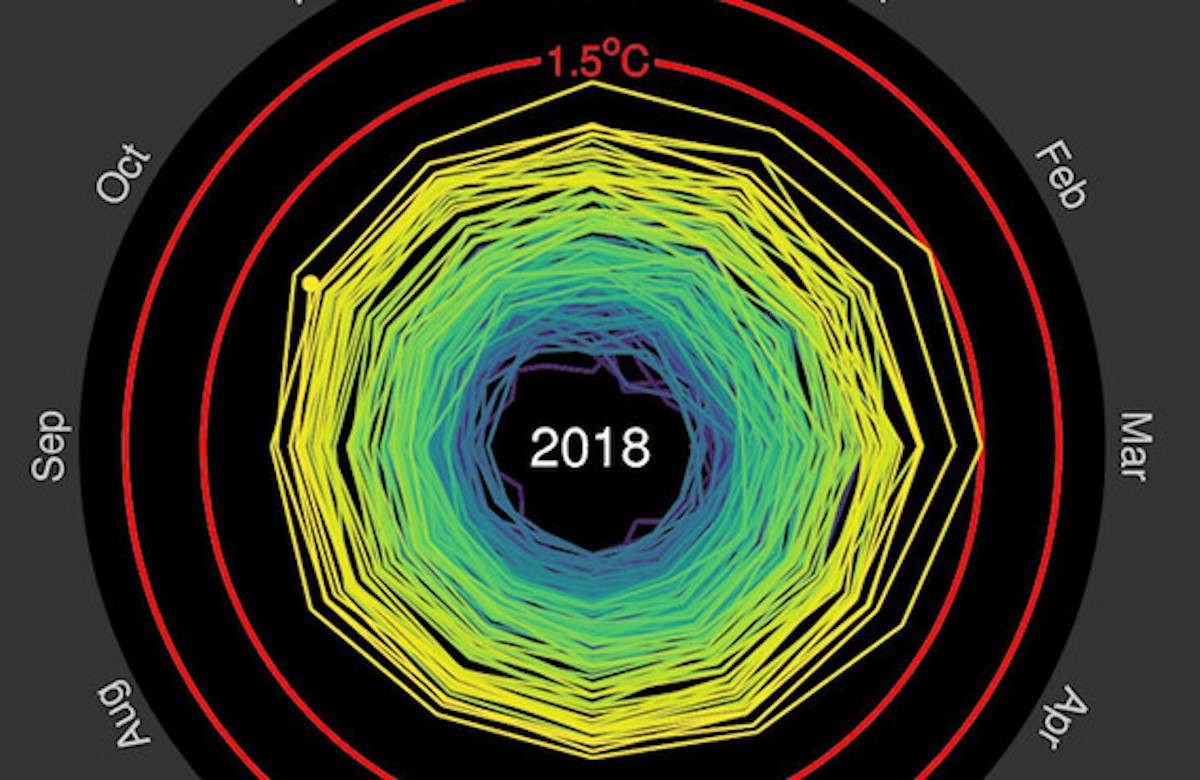感性與機器看似對立,卻在疫情時代中共存,透過科技傳遞情感的案例隨時都在發生,人類因應世界的運轉,做出的回應遠比想像複雜的多。北美館《感性機器:後資本主義時代的自我療癒》抽象的命題背後,策展人李雨潔、林瑀希試圖從 8 位藝術家並存感性和機器概念的作品當中,抽絲剝繭地挖掘內心與外在的對話,展現生物的感性與象徵現代社會的機器共處及溝通的方式。

▶ 展覽介紹|北美館《感性機器》!打造後疫情時代釋放情感場域
李雨潔表示:「藝術的其中一個面向就是幫助大家找尋一種情感釋放的空間,這正是展覽標題中有關後資本主義時代官能以及情感的『自我療癒』的指向,不一定是「共情」,反而是人們在各自所見的風景中,回應他人的故事。」因此展覽可被想像為一個療癒機器的總體,在藝術作品裡看似對立的現象、儀器或者情緒感受中,找到內外在衝突中的平衡。
本次 La Vie 採訪了3組參展藝術家,貼身了解作品背後的故事與思維,以及在疫情時代下如何以藝術反映世界的變化。以下由展出《床外的藍天》的台灣藝術家陳慧嶠、《太初有道》與《資訊——人類基因之 IXX 染色體段落,上帝發布神聖計畫》等作品的越南藝術家綠橘(Cam Xanh)、《菩提與榕之下》的新加坡藝術家組合朱浩培/李長明帶來Q&A。
La Vie:面對本次展覽主題「感性機器:後資本主義時代的自我療癒」,您腦中浮現的第一個想法是什麼?與您展出的作品如何連結呢?
陳慧嶠:首先讓我雙眼定焦的是「機器」,接著在我腦海浮現的是「時間」。時間或許源於人類對自然規律的洞悉與領悟,而現實中可計量的時間是人為概念,於日常生活中已然成為一種慣性或機械式的反應。我們都在時光機的運轉中臆想未來或回溯過往。對我而言時間是永恆的移動之像,亦是心靈知覺、記憶與預期的延展,有如一場遙遠的、私人的夢,於是我本能地提出《床外的藍天》(2018)這件作品參展。

綠橘:這個主題對我來說是一個無可避免的行為與必須面對的課題,尤其身處在這個看似即將崩毀的世界。我覺得自己好像掉進一個黑暗無光又深不見底的隧道中,卻又深知總會有希望。於是,我閉上雙眼潛入內心深處,尋找著光照進來的裂縫,從一道光芒中,再漸漸地發現更多彼此相連的裂縫,就如同世界上數十億人彼此之間也是相互連結著,我們全都是這個「巨大又破碎的機器」的一部分。經歷了這些苦痛,我知道我並不孤單,我們每一個人最終都能找到那束光,藉由療癒他人的過程,也療癒了自己。

李長明:在全球居家遠距的時期看到這個主題,我聯想到「感性」與藝術的關係不能僅依靠螢幕,而需要人們親身且實際的體驗,這和我們本次展出的作品《菩提與榕之下》如何被呈現有關係。我們很重視攝影作品在空間中的狀態,以及觀者如何理解、與作品相遇的情況,進而產生什麼樣的想法,因此更強調這件作品應該要親自互動觀賞,以形塑出個人的情感體驗。

La Vie:請與我們分享本次展出的作品中,一個不為人知的小秘密或巧思吧!
陳慧嶠:《床外的藍天》這件作品首次展出是在空總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的展覽,靈感源自我受邀到蘇格蘭駐村三個月的經歷。我的外文能力極差,卻能和策展人Andy Fairgrieve 以比手畫腳或隨意的一個發音理解彼此,有種不可思議的熟識感。回台灣後,我找知名的前世今生諮商師 Bruce Allen 把脈,得知原來前世的我是英國一戰的飛行員,和作為後勤的 Andy 是知己好友。我相信這個說法,是曾經有對原先不認識的兄弟送我一只一戰的飛機螺旋槳,這除了與我夢境中的飛行吻合,也跟我後來得知的前世經驗相連。簡言之,這件作品和前世今生有關,也與空中軍事武力的發展有關。

綠橘:本次展出的《共鳴 #84》是一件聲音裝置作品,創作時我召集朋友一起聆聽,有位朋友說讓他想起了 NASA 的無人太空探測船「航海家 1 號」。航海家 1 號記錄了地球上的圖像和聲音,如同時光膠囊一般向外星人講述地球的故事,在 1977 年發射至外太空,而那年也正是我出生的一年,至今它仍是距離地球最遠的人造物,儘管它的運轉軌道和速度已經遠離太陽系而無法再回到地球,它仍持續回傳星際介質與太陽風的互動。2021 年 5 月 10 日,科學家宣布航海家 1 號從回傳的訊息中檢測到來自太陽的「嗡嗡聲」。聽說星際介質就像是一場安靜的小雨,我詩意地想像著航海家 1 號在星際旅行時,終於遇見命中註定的星際介質而回報的情況,而《共鳴 #84》這件作品的靈感就來自於這個宇宙的「嗡嗡聲」。

朱浩培:我們攝影作品中的破碎觀音神像被沖上岸後,每次我們回到同一個地點,神像總是如初,只是位置不停地改變,有時在樹下、樹枝中,有時則在海灘上,不知怎麼地,祂總是能躲過被清潔的命運,彷彿自然地或超自然地找到祂的出路,但其他的神像卻消失了。這種神秘的感覺對我們來說很有意思,代表著包含人為、自然力量、超自然現象都有機會參與這尊神像的移動過程,為這件作品帶來更多耐人尋味之處。

李長明:有一天我們為了作品在尋找樹木神龕時,我不小心被昆蟲螫傷了,兩天後我的手腫得看起來像是炸裂的手套,我趕緊去看醫生,也因此住院了 2 天。醫生認為我只是對於蟲螫過敏,但我卻迷信地認為這是一種暗示,警告我們不該那個地方尋找神龕。
La Vie:在疫情時代下是否有一些反思呢?也是否因此有了全新的創作,或者有機會呈現於未來的作品中嗎?
陳慧嶠:在疫情與死神的逼臨之下,我的感受是藝術在現實中幾乎使不上力,除了自我療癒。在創作上對於未來,我無法想像和預期......。
綠橘:本次展出的作品皆是在疫情時代下誕生或發展而來。而我認為,從現在開始,任何創作都無法擺脫它了,因為疫情徹底改變了涵蓋藝術領域的整個世界,甚至已經成為我們的一部分,而我們目前僅在這段自我療癒旅程的開端而已。此時正是時候反問自己:「藝術是否如以往所相信地那般必須存在呢?」我敢肯定的是,儘管世界仍存在著那麼多的不確定性,仍會有光芒、樂音與智慧,就如同我聲音裝置作品《共鳴 #84》所表現的,也一定會有愛。

李長明:由於新加坡封城,我多了許多待在家的時間,比起部分朋友感受到的焦躁不安,我發現我很享受在家中閱讀、看電影,也養成了晚間散步的習慣,幫助我釐清思緒並獲得新想法。在疫情期間,我經營的小型獨立出版社 Nope Fun 也同步與朋友進行著 LGBTQ 的攝影書出版計畫,亦希望能將我以往的攝影作品出版。

朱浩培:我同樣增加了不少居家生活時間,並讓我開始在空地上從事園藝植栽,一邊種植時,我一邊會思考植物如何能與我接下來的創作結合。我持續進行我原有的長期創作計畫,也在封城期間嘗試以線上的方式實驗藝術,這肯定會影響往後創作與人們互動、對話的形式。
文|Diane Tang
圖片提供|北美館 部分攝影|簡梵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