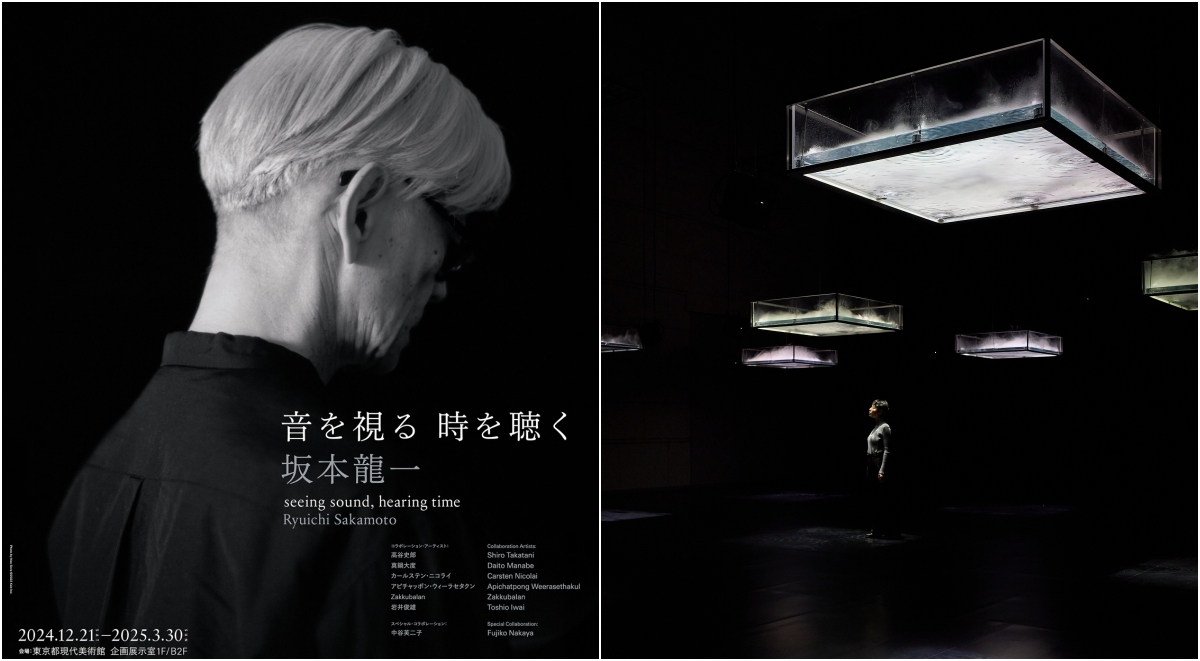林楷倫是作家也是魚販,以寫作獻上產地直送的《偽魚販指南》;前性工作者袁非(涼圓)是小說原型人物,最後也成為自己的著作《手槍女王》女主角。而港都藍領子女謝嘉心則因研究,重新認識《我的黑手父親》與自己。當解密百工百業的著作持續湧現、《做工的人》甚至改編成為電視劇,一股不可忽視的書寫職人文學風潮走入大眾視野。
職人,擁有技藝的工作者,常是被報導、取材的對象,近年卻湧現一批職人化身作家。2017年,林立青以素人之姿在寶瓶文化推出散文集《做工的人》,隔年統計售出超過40刷、5萬本,甚至在2020年改編為同名電視劇。在林立青之後,寶瓶文化持續推出接體師大師兄、洗車工姜泰宇等人的作品,到今年有林楷倫《偽魚販指南》;各家出版社也紛紛發掘鐵工曾文昌、警察一線三、命案清潔師盧拉拉、計程車司機王國春等職人,去年袁非(涼圓)在大辣出版的《手槍女王》,更帶來性工作者的親身故事。

這些職人作家頻頻闖進博客來、誠品網路書店銷售榜,蔚為一股風潮,以親身經歷的「真」為基底的創作,衝擊了專業記者、學者與作家創作散文與報導的非虛構文學傳統。而近年,另外有關注社會議題的出版社,從學術領域中發掘素人,將論文改寫為面相大眾的文學作品,如群學《血汗超商》以及游擊文化的《靜寂工人》等,游擊文化更在2021年推出《失去青春的孩子》、《萬能店員》及《我的黑手父親》3本著作。這些書寫職人的著作,成為我們拼湊台灣百工模樣的拼圖。
書寫職人的生活如此
3月甫出版《偽魚販指南》的林楷倫,說沒有人天生喜歡賣魚,在臉書貼文上他強調:「我討厭的是沒有選擇的自由。」家庭是枷鎖,他的賭徒父親留下無底洞一般的債,迫他接下家中魚攤。最初林楷倫並非心向寫作,反倒想深入社會學研究,考上研究所卻又因父親再次的龐大債款必須放棄,直到33歲才決然離家自行創業。「生活如此,我不能一直掉進去,掉進去我就毀了。」一忙就是3、4年,債還了他放緩工作腳步,寫作成為抒發,「生活很苦欸,我爸這種事情不寫會憂鬱。」然而他認為賣魚是他「理性的選擇」,賣魚維繫了生活,其中苦澀也不乏甘甜,如同書中寫與生意夥伴的信任,也有與妻子的互動。

2020年才「上岸」離開八大行業,《手槍女王》作者袁非筆下的慾海闖蕩記不全然沉重,甚至偶有尖銳又不失幽默的觀察與吐槽。她生自吸血鬼般的家庭,一度連身分證都沒有,面對巨大的生存壓力,「打手槍是我那時候能選的最好的工作」,自此下海半套店(男士護膚店),被喚作「涼圓」。幹部前輩曾對她說:「我們要多做善事,因為我們的錢不是那麼乾淨。」彷彿她們就是陰溝裡的老鼠,私下做再多公益在岸上仍見不得光,她不甘心也很心疼。寫作的渴望源自於巨大的恐懼感,當袁非成為陶曉嫚小說《性感槍手》的原型人物並被收錄在訪談輯出版後,她身旁幾個同事卻相繼離世,「我害怕隻字片語都沒有留下,我們的痕跡就在世上消失了。」外界的正面回饋讓她有了勇氣,同時在陶曉嫚的鼓勵下,她決定開啟「手槍女王自白書」粉專書寫自己。停筆多年的林楷倫也曾對寫作沒信心,直到參與「想像朋友寫作會」刊登專欄,意外獲寶瓶文化總編輯朱亞君注意,被問到出書的意願,那時他還沒獲得林榮三或任何文學獎,「寫作讓我得到最多的是有人肯定你的才能。」

不同於前兩者,謝嘉心並非職人作家,《我的黑手父親》是由她的研究所論文改寫而成。她的父親是拖車師傅,平常製造、維修拖板車,即所謂的黑手。「不讀書就做工」,從小父親總以自我貶斥告誡她,她深受影響,循著升學路徑脫離藍領階層,又因為研究回望自身家庭。她在書中坦言最初的狂妄,曾想藉訪談師傅們批判勞動現場的辛勞與不義,但進入現場才驚覺師傅們是各憑技藝、能自信養育家庭的「技術工人」,哪需她代為鳴不平?這讓她一度內心困窘掙扎,論文方向也轉為從她的觀察中發掘自己成長的背景。決定與游擊文化合作出書後,改寫時間就長達5年,承接他人的生命故事總是沉重,尤其是面對是自身家庭與父母,寫到、講到時常掉淚,對她卻也是珍貴的機會,「因為有了對話空間,所以好像跟他們的距離變近了。」
真實就在書寫與被書寫之間
職人作家基於親身經驗、主觀的「真」,成為他們作品的引人處,林立青即在《手槍女王》推薦序中點明這種力量源自他們「比記者蹲得更久,比學者懂得更深。」袁非以被陶曉嫚書寫的經驗說明,外來作者沒有現場第一手經驗,難以完整還原,「像我們的說話語氣會跟記者轉化後的敘事會不一樣,再加上記者會顧慮我們的產業性質與感受,寫作會有所取捨。」謝嘉心非常清楚作為研究調查者限制,自承短促的訪談無法收盡師傅們數十年的故事,由旁觀者側寫的細膩度必然減少很多,「我永遠無法成為我的觀察對象,再努力想要融入,也永遠不可能知道他們在真正的工作滋味與生命經驗。」

林楷倫也認為有些角度只有身處其中才能看見,但身為職人作家,不會怕寫作摻雜過多主觀而有觀察者偏差?他本不追求全然客觀,而是要讀者先跟著他直接去聽市場的吵、聞市場的臭,感受那些體溫。「我的寫作像是攝影機在旁邊看著,又不時介入進去。朱亞君曾對我說:『你的寫作讓人感到一點疏離,但那疏離才是魚販最真實的樣子。』疏離,是因魚販們在商場上共享同伴情誼、下班後生活又彼此錯開,他不過多揣測只寫職場所見。袁非也說,曾有讀者認為她的文字過於疏離、情緒張力不夠很可惜,但小姐們各自或有沉痛或複雜境遇,她們麻痺自我慣了,「疏離就是我們這行的特性,所以我把語氣保留起來。」而且她喜歡日劇《深夜食堂》的旁觀敘事,所以適度收斂自己的情緒,不想讓筆下人的複雜性淪為非黑即白,「我只負責說故事,你自己去感覺。我過多引導,那就失去意義了。」

論文寫作必須極盡客觀,嚴謹地回應提問,但改寫的散文著作就能融入軟性、主觀。隨著謝嘉心畢業,她對照自身的白領職場經驗有了更多感悟,她不能深入其他師傅的人生,就寫入更多自己與家庭的故事,此時褪去研究者的客觀外衣,女兒與家庭的角色立體浮現,「書寫家庭的段落反而得到更多回饋,其實人們對拖車師傅的職業不一定在意,卻從書中找到自己家庭的影子。」她的家庭史就是台灣自農、工到白領社會變遷的縮影,從中或許照見了一代人的集體經驗。
真摯地消費他人與自己
那麼究竟該怎麼看待「職人」兩字?林楷倫認為「職人應該要意指工匠,而不是階級。」外界不應由上而下簡化他們成為沒有生活選擇的人,他平視的筆下,許多魚販擁有「自由意志」、勇於承擔生活而各懷本事。袁非舉例從事「手工業」不能只靠青春美色,如書中蘭姐透過有技巧碰觸皮膚的「輕功」就需要時日磨練,她們也是職人,只是處理社會暗面的慾望,而且坦言自己不能代表整個八大行業,在性服務上,還有酒店、全套店等等細緻歧異。

目前從業文化資產保存領域的謝嘉心,最終理解父親這輩技術工人貶抑自己,是他們由農轉工、期待子女擁有更好生活的簡單心願,然而百工並無好壞之分。書寫職人不免面對讀者獵奇心態、消費自身與他人的生命的各方質問。謝嘉心以研調者的角度,肯定書寫職人的實踐,相信能從中拼找台灣的社會脈動,「要非常感謝他們願意講出別人不一定願意說的故事,彌補我們的無知。」

林楷倫並不否認是在消費自己的生命經驗,認為不攤開自己,就不可能看到藏在背後的故事,這也是以小說得獎的他,卻先出書散文集的原因,「寫散文比較沒安全感,你必須暴露自己。我小時候常隱藏魚販的身分,那得自問為什麼曾覺得身為魚販是羞恥的?」非虛構的散文面對真實的人,虛構的小說則推進讀者想像的疆界,他已規劃未來的小說創作,也笑說若有機會像《做工的人》改編IP,他都想好招了,就像他在書裡〈魚之占卜〉中玩他的創意。

現身讓袁非的作品有了真人認證的力道,卻也讓從業中的同伴有所顧忌而遠離她。她當然想藉由寫作獲得認同,「說我想紅也不為過,我確實希望更多人看到這些故事。」岸上的光亮或許還過於刺眼,她慢慢適應,經營藝人事業、在擒慾實驗所教學「輕功」⋯⋯或許還想寫岸上生活記,儘管能給出的有限,她想讓更多人理解性工作者,藉機也告訴有相似際遇的人可以這樣走過來,「最棒的是當你買下一本書,就能看見不同的人生,也因為有這些願意去看見、心胸開闊的讀者,我們才能活下去,這些東西才有被出版價值。」
林楷倫
1986年生,想像朋友寫作會的魚販。林榮三文學獎2020年短篇小說首獎、2021年三獎,時報文學獎2021年二獎、台北文學獎、台中文學獎等。著有《偽魚販指南》。
謝嘉心
七年級生,高雄市小港區人,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財團法人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執行長。碩士論文《「做師傅就好」:港都黑手師傅的生命、工作與社會流動》獲得臺灣社會學會碩士論文佳作獎、碩士論文田野工作獎、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碩士論文優秀獎。著有《我的黑手父親》。
袁非(涼圓)
30世代的女孩,本名並不重要,在台北做夢及創作。夢中和筆下的台北略與工作經驗相同,而不確定讀者會從她的文字中看到哪一個世界。著有《手槍女王》。臉書專頁:手槍女王自白書。
文|吳哲夫
圖片提供|寶瓶文化、游擊文化、大辣出版
更多創業幕後、品牌經營新知皆在 La Vie 2022/5月號《創業者的冒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