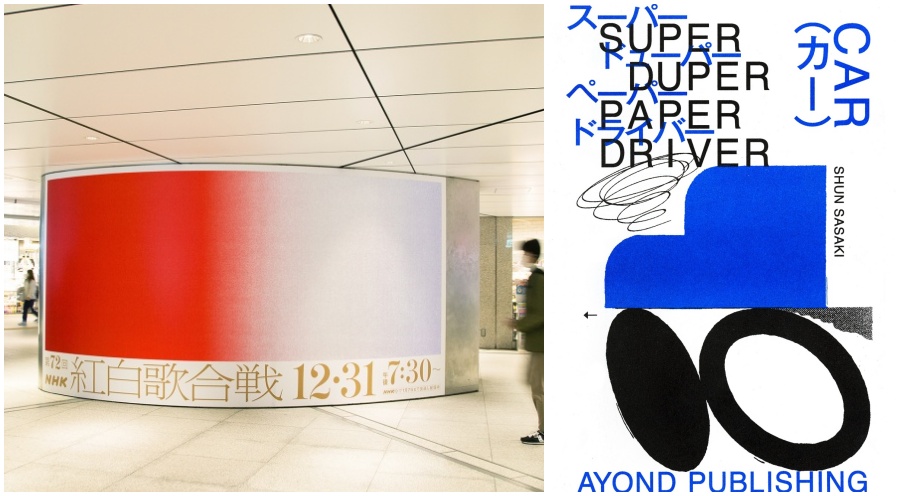溝通,對鄭宜農而言,從來都是困難的事情,從《海王星》到首張全台語創作《水逆》,她持續尋找與世界溝通的姿態,用力地突破人們彼此的隔閡。
很難定義鄭宜農,獨立音樂創作歌手、編劇、演員、作家⋯⋯不同的身分都是她。16歲時創作的《風中的小米田》短篇劇本被父親鄭文堂導演引用拍攝,成為他得獎最多的片;19歲編劇並出演他的電影《夏天的尾巴》, 提名第44屆金馬獎最佳新演員;2019年以《玉仔的心》拿下金音創作獎另類單曲獎;2020年出版第二本散文集《孤獨培養皿》。

在「水逆之後呢?」小巡迴前夕,她在Instagram上面直播說道:「我每個時期都不一樣,我是變動星座(雙魚座),近期像是透明泡泡的感覺,上面散逸著彩虹般的光。」姑且用星座做解釋,對宇宙學興趣濃厚的她自我詮釋:「我的星盤:(太陽)雙魚、上升巨蟹、月亮天蠍,三個水象星座,就是一個完全感受性的人。」因為感受很強、接收很多,從小她需要藉由創作消化感受,與世界互動、向外界溝通。溝通對她從來都是困難 的,但她發現不只她自己,原來每個人都會遇到溝通的障礙。水星在星象中主司溝通,當水星逆行時,溝通受阻、電器失靈而諸事不順,而「溝通」正是她以此命名的全台語新作《水逆》所要探索的題目。

溝通從來都是困難的
溝通是什麼?人為什麼會那麼用力、渴望地溝通?「這源自於我們每個人都希望獲得理解,或者人都害怕孤獨。」專輯開頭的〈人如何學會語言〉,啟發自作家吳明益小說集《苦雨之地》中的同名短篇,寫一個熱愛自然的自閉症少年,能聽音分辨鳥鳴、成了鳥類專家,卻因故失聰,再也聽不見陪伴他的鳥語,「那是一個很孤寂的過程,可是他沒有放棄,還是超用力地,要把他看見的東西傳遞出去。」絕望中仍抓住那道微光,少年以手語去表達鳥語。讀完文章,與她的成長經歷有那麼多共鳴,她哭了,當天就把這首歌寫完。
「我小時候也是住山上,大自然的語言對我而言比人類語言還要熟悉,很長一段時間我覺得跟這個世界的溝通有一層隔閡。」生於創作者家庭,鄭宜農成長中與群體交集卻也錯開,如同國中放學後,同學們都往山下補習,只有她往山上走,暗夜中一個人與星星與蟲子說話。

她的專輯都以星體命名,不同的星體正巧對應她各階段的狀態。19歲的她開始寫歌,首張專輯《海王星》不想被命名成「同名專輯」,因而誤打誤撞發現雙魚座的守護星正是海王星, 像那時仍朦朧迷幻、彷彿在星系邊緣行進的自己。 她仍在摸索,《Pluto》(2017)是她歷經心風暴、與世界碰撞的結晶。冥王星象徵置之死地的重生,鄭宜農直面真實的自己後更有力量,主導專輯製作、音樂元素更多元奔放,並開始和外界大量合作。「我隱約都知道,我需要一些碰撞來加強我自己。」她同時也組團「猛虎巧克力」、參與特殊企劃「小福氣」, 持續摸索與他人溝通的可能。「寫完《Pluto》後,我覺得對『自我』探求到了一個程度,不想只講自己了。」
她更試著擁抱群體,天王星正是代表群體意志的行星,《給天王星》專輯名稱在星體之外多了「給」的動詞,這是鄭宜農對自己的宣示:給出自己,我要開始講更大的事情了。到了 《水逆》,「逆」是感受孤獨的普遍性,任何人都可能有溝通受阻的時候,11首曲目由抓住光亮的〈人如何學會語言〉、探討女性社會標籤的〈新世紀的女兒〉,來到情緒陰暗低盪的〈天已經要光〉、〈親愛的〉,呈現溝通中的憤怒、混亂與不安,最後再逐漸帶回溫柔、明亮的光景,寫家庭記憶的〈囡仔汗〉、〈做風颱〉⋯⋯她從各面向發掘溝通的不同樣態。

台語創作是場無限拉扯
問她為什麼這次堅持全台語創作?鄭宜農坦言自己台語並不好,用不熟悉的母語挑戰自己,也是種「逆」的體現,「我必須要超用力才能去激發更深層的溝通,『超用力』就是《水逆》想要講的事。」這是她的玩心。 她最早的台語創作都是因緣際會的需求,如〈莎喲娜拉〉是她為父親執導、她參演的電影《眼淚》所配的片尾曲,與她對戲的蔡振南在聽完後,鼓勵她:「妳要多寫台語歌,年輕人都不寫台語歌了,尤其很缺台語歌手!」第二首為《奇蹟的女兒》片尾創作的〈玉仔的心〉時,她嘗試將電氣音融入台語歌的可能性,到了日後feat.陳嫺靜的〈街仔路雨落袂停〉,她更有了經驗與自信,換掉原本的華文歌詞,寫成了一曲輕盈的台語嘻哈。這並非刻意回應外界的期待,更多是「創作宅」探究的心態。這也是補償她小時沒辦法用台語和阿嬤好好說話的遺憾。在散文集《孤獨培養皿》中,她曾自剖到,小時在台北就學時,講台語隨時會被嘲笑的自卑感, 讓她對學習台語彆扭,「我一直很遺憾,自己沒有跨越語言障礙多理解她。」透過台語歌的創作,她感覺接近了阿嬤一點,她的台語也越來越輾轉(liàn-tńg)了。

然而,全台語創作談何容易?倒音、咬合問題難以克服,有歌詞甚至在進錄音室前還重寫了2/3,要熟悉不同於華文的俚白表達方式更不容易。「頭洗下去了,只好想辦法完成了。」她也在語言的傳統與創新之間無限拉扯,譬如〈新世紀的女兒〉歌詞中「理想是甜甜的孤味」,「孤味」原指店家專注做好一道料理的匠心,她卻挪用電影《孤味》(2020)為詞面衍生出「為信念堅持,伴隨孤獨也沒關係」的複層新涵義,「只要能理清自己的脈絡,去挑戰用母語創作、把它變得不像大家從前想像過的母語,這件事情就是成立的。」語言是活的,創作者會有取捨跟堅持的過程,這會為語言注入延續的活力。鄭宜農非常佩服阿爆(阿仍仍)創作《Kinakaian母親的舌頭》時,堅定挑戰各種新元素的實驗,直面族語傳統的爭議,促使她主動寫信出擊,親自邀請阿爆在〈或許就變成書裡的風景〉中一同對唱。爭論中,或許也產生對話的可能,「創作的多元性正在建立,期間一定會遇到各式各樣的衝擊,所以大家就擔待點囉!」
看見更加豐饒的音樂場景
「創作跟人生階段之間的關係是騙不了人的,我無法回頭去寫已經過去的東西,所以只能寫當下,那我個人的成長就很重要,如果沒有成長,我就無法突破。」鄭宜農迎向世界的姿態更趨熟稔、堅實,當她將感知的觸覺向外延伸,她看見的,是台灣的音樂文化場景,正在眾多創作者的澆灌下日益豐饒。在這個自品牌與自媒體的分眾時代,資源更加平均分配,可能性無限。

對此,鄭宜農也「無限開放」自己。「我不一定是最有影響力的那個人,可是我想要參與其中,當滾動這場景的其中一份子。」她思考能如何為這場景帶來久遠的影響:近期她與阿爆輪番主持KKBOX的podcast節目《潮流新聲Rising Star》,希望帶領聽眾認識更多的年輕創作人;也為迷走工作坊在嘖嘖平台上募資的《台北大空襲》電玩譜寫主題曲〈終戰〉,讓不同領域的能量交互激盪。身在這樣眾聲喧嘩的音樂場景中,變動星座的她希望自己未來成為「變動成功的存在」,「我想要當一個很具包容力的人,永遠可以變成不同形狀跟人溝通,然後創造出各種創作的可能。」
「但是無人看見的所在/就欲予你乘歹/彼的孤單恰鬱卒/攏予你按奈」,在專輯末尾,鄭宜農讓〈無人看見的所在〉延續前曲的和絃,彷彿在說溝通在經歷一切困難之後,獲得一個溫柔、開闊結局。問她如此用力透過創作溝通,至今是否還會感覺孤獨?鄭宜農說現在面對世界更有信心了,但,「我始終會有新的發現,始終會有無法明確說出的感受,那是身為人都會面對的課題,所以只要活著,我就會持續創作。」那份孤獨還是會存在,只是現在的她並不覺得不好,甚至有點享受。

鄭宜農
台灣獨立創作女歌手、演員、編劇。 2007年以電影《夏天的尾巴》出道, 並提名第44屆金馬獎最佳新進演員。著 《孤獨培養皿》等。曾組樂團「猛虎巧克力」、Special Project「小福氣」;發行個人專輯《海王星》、《Pluto》、《給天王星》、《水逆》。
文|吳哲夫 攝影|鄭弘敬
圖片提供|火氣音樂
妝髮|顏維音 Wei Yin Yen
服裝協力|Dleet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La Vie 2022/4月號《給下一代的設計》